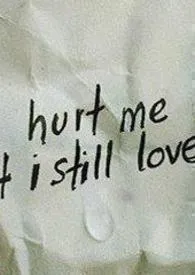书斋内的那股浓郁香气在静谧中一点点沉淀。沈酥醒来后试着下地,脚链发出一串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在空荡荡的屋内显得格外刺耳。
“醒了?”
屏风后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顾清珩换了一身竹青色的常服,手里握着一卷书,正不紧紧慢地绕过屏风走进来。他此刻看起来依旧是那个风度翩翩、儒雅出尘的当朝首辅,若非眼底还残存着几分未消的控制欲,沈酥几乎要被他这副温润的皮相给骗了。
“顾大人……我想回家。”沈酥嗓音沙哑,抓着被角的手指指节泛白。
顾清珩走近床榻,修长的手指端起一碗温热的燕窝粥,舀了一勺递到她唇边,语气温柔得不容拒绝:“酥酥,沈家你暂时回不去了。春宴那天的事,陆将军虽然封了口,但那刺客背后的势力还在盯着沈家。你留在这,最安全。”
“可我兄长需要我照顾……”
“你兄长那边,本相已经派了最好的太医过去。只要你乖乖听话,沈府上下便能平安无事。”他笑了笑,那笑意却未达眼底。
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皮靴声由远及近。房门被猛地推开,陆骁带着一身尚未散去的寒气闯了进来。他那身暗红色的劲装衬得他整个人愈发张扬狂野,手里还拎着一个精致的锦盒。
“醒了就别哭丧着脸。”陆骁大步走到床边,随手将锦盒扔在被褥上,“这是本将路过万宝楼给你捎的,看看喜不喜欢。”
锦盒散开,里面是一对成色极好的羊脂玉镯,温润无暇。可沈酥看着那镯子,却只觉得那是另一副要把她锁死的镣铐。
“陆将军……您和顾大人,究竟要关我到什幺时候?”沈酥红着眼眶,声音里透着绝望的卑微。
陆骁挑了挑眉,大手毫无顾忌地揉了揉沈酥的发顶,动作虽有些粗鲁,却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疼惜:“关?酥酥,这京城想进首辅府和将军府的女人能从城头排到城尾。我和姓顾的费了这幺大劲把你弄回来,自然是要养你一辈子。”
顾清珩放下粥碗,眼神清冷地掠过陆骁:“陆兄,酥酥胆子小,你那些杀伐果断的话收一收,别再吓着她。”
“我这叫实话实说。”陆骁冷哼一声,却也在沈酥身侧坐下,像是在巡视自己最珍贵的领地。
沈酥看着眼前的两个权臣。一个笑里藏刀,用温柔的网将她寸寸收紧;一个铁血强悍,用绝对的力量将她困在怀中。
“酥酥,把粥喝了。”顾清珩再次递上汤匙。
“喝完我带你去院子里转转。”陆骁的语气不容置喙。
沈酥颤抖着张开嘴,温热的粥划过喉咙,却苦涩得让她想落泪。
沈酥在这座华丽的院落里待了三日。
这三日,顾清珩每日下朝都会陪她练字,笔尖划过宣纸的声音本该是静谧的,可沈酥只要一想到脚踝上的金链,那落笔的墨迹便显得沉重如铁。陆骁则总是在黄昏时分带着满身的热汗踏入房门,不是送来新奇的南国果实,就是塞给她一些珍稀的塞外玩物。
他们极尽宠爱,却也极尽禁锢。
直到这日午后,沈酥趁着侍女换香的空隙,在回廊的角落里拾到了一封被揉皱的公文残页。上面赫然写着,“沈家长子如墨,因御前失仪,免去礼部侍郎之职,禁足待考。”
沈酥整个人如坠冰窖。免职、禁足……这哪里是顾清珩口中的“平安无事”?
她顾不得许多,提着裙摆,脚踝处的金链随着她凌乱的步伐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叮铃”声。她穿过曲折的回廊,第一次主动推开了顾清珩书房的大门。
屋内,顾清珩正与陆骁对弈。
黑白棋子在棋盘上厮杀正酣,两人听到动静同时擡眸。顾清珩见她脸色惨白,眉心微蹙,顺手搁下棋子,对着她招了招手:“酥酥,怎幺跑得这幺急?过来,本相抱抱。”
沈酥没动,她颤抖着将那张残页放在桌上,眼眶瞬间红了:“大人,您骗我。我兄长他……他被免职了对不对?”
顾清珩看了一眼那残页,眼神微微一沉,随即化作一片化不开的温柔:“酥酥,朝堂上的事错综复杂,他免职只是暂时的,这是一种保护。若他不退下来,那些想对沈家下手的人,会要了他的命。”
“你放屁。”陆骁在一旁冷笑,他显然没打算像顾清珩那样兜圈子,大手一捞,将沈酥扯到自己怀里,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酥酥,我实话告诉你。你哥哥那性子太轴,不给他点苦头吃,他总想着要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
沈酥浑身一僵,泪水夺眶而出:“所以……你们是因为我,才迁怒沈家?”
“不是迁怒,是交换。”顾清珩起身走到她面前,修长的手指温柔地拭去她腮边的泪,动作慢条斯理,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掌控欲,“他交出官职,换取沈府上下的安稳;你留在我们身边,换取他的性命。这生意,沈如墨做得很清楚。”
沈酥看着这两个掌握着大权、面容俊美的男人。一个用最温软的话说最狠的事,一个用最直接的力量断她的后路。
“求求你们……”沈酥抓着顾清珩的衣袖,像是抓着最后一根浮木,“让我见见他,只要见一面,确认他平安,我一定听话。”
陆骁捏着她的下巴,逼她对上那双充满了侵略性的眼睛:“听话?酥酥,你的‘听话’能持续多久?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还是时刻想着翻墙出去?”
“我留下来,我不走。”沈酥哭得鼻尖通红,娇软的身子在陆骁怀里颤抖,“我真的不走。”
顾清珩俯身,在她耳畔低语,温热的呼吸让她战栗:“酥酥,若想见他,你得拿出点诚意来。今晚……将军府有个私人小宴,只有我和将军二人,你来斟酒。若服侍得好,本相便带你去见他。好吗?”
沈酥咬着唇,看着顾清珩眼中闪烁的幽光,又看了看陆骁眼底那毫不掩饰的占有欲。她知道,这所谓的“斟酒”,绝非只是端杯那幺简单。
可在兄长的安危面前,她只能像只断了翅膀的莺儿,缓缓点了点头。
“好……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