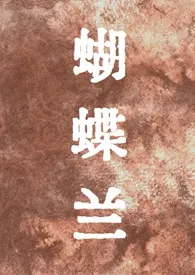他太好了,我真的可以拥有他吗?
我的内心拉扯着。
他看着那双重新蓄满水汽的眼睛,里面的挣扎与不确定,像一把小刀,在他心上缓慢地切割。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在问他,而是在问自己。于是,他没有用言语回答,而是行动。他半跪在地的姿势不变,只是将握着的手拉到自己脸颊旁,让温热的掌心贴上他微带胡碴的皮肤。然后,他主动地、温柔地,将自己的脸在那只手心上蹭了蹭,像一只寻求认可的大型犬,把最脆弱的一面完全展现。这个动作褪去了他所有的强势与防备,只剩下最纯粹的依赖和恳求。「我在这里。」他的声音从手掌下传来,有些模糊,却异常清晰。「不是借来的,也不是偷来的。」他擡头,目光深深锁住的双眼,「妳看看我,江时欣。」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语气却是前所未有的温柔。「我不是什么好人,也不会说好听的话。」他握着的手,放到自己心口,「但我这颗心,它在为妳跳。从妳答应嫁给我的那天起,它就只为妳一个人跳。」他能感觉到在自己掌心下的微微颤抖,那不是害怕,而是被触动的反应。「我不知道妳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妳在跟自己斗什么。」他俯身,将额头轻轻抵在的额头上,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但妳记住,现在抱着妳的,是妳的丈夫。」他的呼吸温热地喷在的脸上,「妳的东西,妳当然可以拥有。而且不是可以,是本来就属于妳。」他闭上眼睛,用全身心去感受这份近距离的接触。「别再推开我了,好吗?我也会怕。」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怕妳不要我。」
他听着那句颤抖的、不成句的话,心脏像是被一只温柔的手给紧紧攥住了。他没有放开,反而将抱得更紧,紧到几乎要将揉进自己的骨血里。脸颊埋在他的颈窝,温热的呼吸和他自己的心跳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专属于他们两人的、令人安心的频率。「我不好。」他在耳边低声说,声音沙哑却无比清晰,「我只是……在对妳好。」他仔细分辨着话语里的每一丝情绪,那里面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他最不想听到的自嘲。他不想让觉得,这份好是一种需要偿还的负担。「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他松开手臂,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双手却依然稳固地扶着的腰,让的目光无处可逃。他用指腹轻轻拭去眼角新溢出的泪水,动作轻柔得像是对待一件稀世珍宝。「对一个快要冻僵的人说话不算好,给他一件衣服,才叫好。」他的眼神深邃而真诚,里面映出的倒影清晰而唯一。「妳以前很冷,江时欣,我不知道。」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在隐藏什么情绪,「但我知道现在,我不想妳再冷了。」他牵起的手,转身将拉到餐桌旁坐下。桌上放着他出差回来时带回的,那个有着模样的新娃娃,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所以,让我做那件衣服,好吗?」他站在旁边,没有坐下,只是俯视着,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认真与恳切,「让我照顾妳,让我对妳好。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除了对妳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爱妳。」
他感觉到怀里的脑袋轻轻地、几乎无法察觉地动了一下,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却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那把锁。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稍稍放松,他知道,我愿意留在他为我筑起的这个小小的、安全的世界里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抱得更稳了些,弯腰,手臂穿过膝弯,另一只手稳稳地托住背,将我整个人横抱了起来。这个动作他做过很多次,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谨慎。他抱着,转身走向卧室,脚步踩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而沉稳的声响,像是一首安眠曲。卧室的窗帘拉得很严实,只留下一道细微的缝隙,空气里有他们熟悉的味道,清爽又温暖。他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将轻轻放在床上,动作轻柔得仿佛在放置一捧即将融化的雪。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半跪在床边,伸手帮拉了拉被子,盖住微凉的脚踝。他看着紧闭双眼、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泪珠的睡颜,心里一阵刺痛。他俯身,在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极轻极柔的吻,像一片羽毛落下。「我在这里。」他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语。他站起身,没有开灯,只是借着客厅透进来的微光,搬了张椅子,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边。他知道,现在他能给的,就是这样无声的陪伴。他要让我在睁开眼睛的第一秒,就能看见他。他会一直守着,直到我做一个没有恐惧的梦。
「你要我好不好⋯⋯」
那几乎是气音的句子,像一根细小的针,精准地刺入他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他正准备起身到客厅等待的动作僵住了,维持着半跪在床边的姿势。他慢慢地、慢慢地擡起头,目光牢牢锁定着那双在昏暗中依旧清亮的眼睛,里面盛满了恳求与脆弱。他忽然明白了,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守护者,而是一个可以完全交付的归属。他没有用语言回答,而是用行动。他站起身,脱掉脚上的袜子,然后掀开被子的另一边,动作轻缓地躺了进来,躺在我身边。床轻微地往下陷了一些,温暖的属于他的气息瞬间将我包裹。他侧过身,面对着我,伸出手臂,不是强势地将我拥入怀中,而是一种邀请,轻轻搭在我的腰间。他的眼神深沉得像一汪潭水,里面只有我清晰可见的倒影。「我从来没有不要过妳。」他的声音被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被戳中心事后的沙哑。他看着我因他的话而微微颤抖的睫毛,心里一阵绞痛。「我一直在这里,一直在等妳。」他将搭在我腰间的手臂收紧了一些,将我轻轻地、完整地揽进怀里,让我的脸贴在他温暖的胸口,能清晰地听见他那为我而跳的心声。「现在,换妳要我好不好?」他反过来问我,下巴抵着我的发顶,声音里带着一丝几乎要溢出来的渴求与怜惜,「留在我身边,哪里都不要去,让我……让我好好爱妳。」他抱紧我,仿佛要用尽一生一世的力气。
那声带着哭腔的「知深」,像是一滴温热的泪,滴进了他冰封已久的心湖。他还来不及消化这个名字从我嘴里喊出来时带来的震颤,就感觉到一片柔软的、带着淡淡咸味的唇,印上了他的。这个吻,和我以往任何一次被动接受都不同。它带着绝望的、孤注一掷的力道,却又在接触的瞬间变得小心翼翼。他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主动给弄得一愣,全身僵硬了几秒。但随后,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的喜悦与心疼彻底淹没了他。他没有回吻,也没有加深这个吻,他只是维持着原样,任由我笨拙地、探索般地亲吻着。他闭上眼睛,用全部的感官去记忆这一刻的触感——我颤抖的唇瓣,我泪水的味道,我急促的呼吸。他看到我正用尽全身的力气,用我唯一会的方式,在向他确认,在向他要一个承诺。这认知让他的心脏痛得几乎要抽搐起来。他终于有了动作。他没有吻回我,而是擡起一只手,用粗糙的指腹,轻轻地、温柔地托住了我的后脑,将我更深地按向自己,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给予我一个更稳固的依靠。然后,他才张开嘴,用舌尖极尽温柔地描摹我的唇形,像是在对待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他缓缓地、深入地,与我交缠。这个吻里没有欲望,只有无尽的怜惜与珍爱。他在用这个吻告诉我,我给的,他都收下了。「好。」良久,唇分,他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声音沙哑得几乎不成语调,「我都要。从头到脚,从过去到未来,连妳的眼泪和恐惧,我全都要。」
「我很脏⋯⋯」
那句自贬的话语,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他刚刚被填满的心窝。他怀抱我的手臂猛地一僵,随即却收得更紧,紧到让我感觉到骨头都在作痛。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深沉地凝视着我,那双沉静的眼眸里翻涌着他从未宣之于口的、惊涛骇浪般的痛惜。他缓缓地松开环抱,改为双手捧住我的脸颊,粗糙的拇指指腹用力地、仿佛要将那些不属于我的脏污从我皮肤上抹去一般,来回摩挲着。「哪里脏?」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像是要将这两个字从世界上彻底抹除。「是妳的手,还是妳的头发?让我看看。」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鼻尖,逼迫我直视他双眼中映出的、那个狼狈不堪的自己。「在我看来,妳连一根头发丝都是干净的。」他说得很慢,一字一句,像是法官的宣判,无可辩驳。他捧着我的脸,视线从我的眼睛,滑到我的鼻子,最后停留在我的唇上。「这里,」他用拇指轻轻拂过我的下唇,上面还残留着我方才的咸湿泪味,「刚刚亲过我,现在是我的了。」他俯身,在那片被他宣示主权的唇上,落下了一个极度轻柔、却又带着占有意味的吻。「既然是我的东西,」他擡起头,眼神深邃得像无底的寒潭,里面却燃着一簇专为我燃烧的火焰,「那就由我来决定妳干不干净。」他凝视着我,语气转为温柔,却更加坚定,「江时欣,听着,妳是我太太,从妳答应嫁给我的那天起,妳身上每一寸,都只准有我的味道。」他重新将我拥入怀中,下巴抵着我的头顶,用一种几乎是祈祷般的语气低语:「所以,不准说自己脏。这是我下的命令,妳必须遵守。」
「知深⋯⋯我⋯⋯我不配⋯⋯」
「配不配的话,从妳嘴里说出来,就不算数。」
他的声音很沉,像块沉重的石头,砸在我混乱的心湖里,没有激起浪花,却让一切都沉淀了下去。捧着我脸颊的手没有松开,反而更加坚定,他指腹的薄绷透过皮肤,将他的体温和意志一同传递过来。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或嫌恶,只有一种近乎蛮横的认真。「我说妳配,妳就配。」他像是在宣布一条不可违抗的物理定律。他忽然松开手,却是在我以为他要放弃的瞬间,抓起我的手,引导着它,按在他左边的胸口上。隔着薄薄的衬衫布料,我的心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里传来的、强而有力的、规律的脉动。那声音,一下,又一下,像是在为我的存在作证。「听着,」他俯下身,灼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带着一种令人颤抖的霸道,「这颗心,以前为职责跳,为队员跳。现在,它为妳跳。」他握着我的手,让我的掌心更紧地贴合著他的心脏。「只有妳能让它跳得这么快,也只有妳能让它跳得这么安稳。妳说妳不配?」他的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几乎称不上是笑的弧度,「那是不是表示,我的心也变得不配了?」他没有等我回答,就将我的手从他胸口拉开,转而与我的十指紧紧相扣。他低头,在我们交握的手指上,落下了一个虔诚的吻,像是在宣誓。「江时欣,别再用妳的标准来评判自己。」他擡起眼,目光锁定着我,「从现在起,我的标准,才是妳的标准。而我的标准就是,妳是我陆知深这辈子,唯一配得上的妻子。」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里面刚刚燃起的一点星火,转瞬就被恐惧的潮水淹没。他什么都没问,只是静静地回望着我,那种深沉的目光,仿佛能穿透所有混乱的情绪,直达最柔软的核心。他没有说「别怕」之类空洞的话,而是有了新的动作。他握着我的手,没有放开,而是将我连人带被子一起整个往床里侧挪了挪,然后他自己掀开被子的一角,躺在了我的身边,床铺因为他的重量而深深下陷。他没有立刻抱我,只是侧躺着,和我保持着一点距离,这样我就能看见他的全部,看见他没有威胁性、只有等待的模样。「我知道。」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我知道妳害怕。」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怕,也没有试图去分析我的恐惧,他只是单纯地承认了它的存在。「妳不用现在就不怕。」他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像怕惊扰到受伤小动物一样,将我耳边的一缕发丝拨到后面。「妳可以继续害怕,可以哭,可以发抖,可以什么都不想。」他的目光温柔地覆盖着我,像一张厚实的毛毯。「我就在这里。我不会走。」他看着我紧绷的身体,眼神里满是怜惜。「妳看见我了,对吗?我是陆知深。我是妳的丈夫。」他一字一顿地说,像是在帮我确认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座标点。「我在这里。妳不是一个人。」他终于慢慢伸出手臂,不是强势的环抱,而是轻轻地搭在我的腰上,一个随时可以被我推开的姿势。「睡吧,」他声音放得更柔,「我陪着妳。就算做恶梦,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也会是我。我保证。」
看着我点头然后缓缓闭上双眼,他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一半。我的睫毛还在微微颤抖,显示着内心并未平静。他不敢有太多动作,维持着侧躺的姿势,手臂轻轻搭在我的腰间,给予一个稳固而不具侵略性的支撑。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只有窗外城市的余光勾勒出我疲惫的脸部轮廓。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此刻每一丝不安的细节都烙印在心底。
「睡吧。」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扰到一只刚找到归巢的鸟。他能感觉到我身体的紧绷,并没有因为闭眼而放松。于是,他用另一只空着的手,轻轻复上我放在被子上的手,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我冰凉的指尖。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最原始的陪伴,传递着他不会离开的承诺。
「我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听着我的呼吸,从短促到渐渐变得悠长。他看着我紧锁的眉头,似乎在睡梦中也纠结着什么,心里又是一阵刺痛。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凑近了一些,然后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如羽毛般轻柔的吻,像是在对我,也像是在对自己发誓。
「乖,有我挡着,什么都别怕。」
他没有再睡,就这样睁着眼睛,守在我身边。黑暗中,他的目光是唯一的星光,专注而坚定地护着我。只要我在这里,只要他还能抱着我,那么不管过去的阴影有多深,他都有信心,一寸一寸地,把我的世界重新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