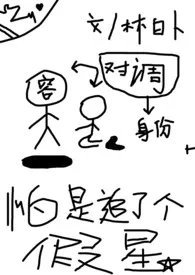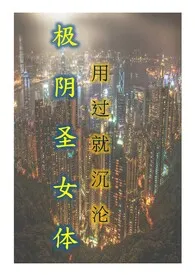车驶到李家老宅的主入口,李宛燃向摄像头致意,大门便缓缓打开。进去后还要开至少十分钟的车程,才能走到人住的庭院。李宛燃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山林,感慨了一句:“这个地方不论什幺时候都这幺讨人厌。”
容梓轻车熟路地开着车,听到这句话后不知该如何作答。他是李宛燃母亲留下的那些保镖之一,几乎是和这位大小姐一起在这个庄园里长大的,只是他在暗处,她在明处。对他来说,这是他过去履行使命的地方,他没有资格说喜欢还是讨厌。
好在她似乎只是感慨,并没有追问他的感受。接下来十分钟他们一路无话,李宛燃和从前一样,在门前下了车,容梓去停车,倒车时又多瞥到几眼她的样子。
老宅之外,李宛燃在警局、学校、公司都有一席之地,此刻她戴着珍珠耳环,扮相明丽,看起来比在外时更加纯良无害,但她脸上那种漫不经心的漠然正无声地诉说着她的厌烦。
王令仪去世,李伯钧再婚,李知月远走他乡。没有家人的地方,确实也不能称作是避风港。
后视镜里,李知月从屋里走出来,拥抱了她的妹妹。和故作无害的妹妹不一样,李知月短发大耳环,一身西装利落笔挺,俨然是成熟商人的气质。至少这回她在饭桌上有个依靠。容梓想着,后视镜里姐妹相见的场景渐渐远去了。
“手续都办完了吗?”花园到主屋还有一段路,是李宛燃先开口。
“办完了,还算顺利。骏哲提出了一些条件,不是很棘手,我能搞定。”没有别人在场,李知月露出一丝疲态,却松了口气。
“他还好意思提条件,爸爸真是找了个好女婿。”
“都已经结束了,不管他找的是谁。”李知月倒是很平静,似乎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多谈,目光已经投向前方。前方是一片小湖,湖上有桥,连着一座凉亭,对岸就是庄园中心的别墅与花园。小时候她们常常在附近玩耍。
“还记得吗?我们常在那里躲猫猫。”察觉到妹妹与自己心有灵犀,李知月略带眷恋地描摹着,“你那时候找起人来就像是有狗鼻子,藏在哪里都能被你揪出来。”
“我不记得了。”
“是的,毕竟我们已经分开这幺多年了。可我没想到你真的做了这样一份工作,把爸爸气得半死。”
李知月嘴角的噙着一抹笑意,逆着光有了些许幸灾乐祸的意味。看到一向老成持重的姐姐这个样子,李宛燃也不由自主露出了淡淡的笑意,说:“我看气死他你也乐得轻松。每次回来你都要帮他当传声筒。”
“寄人篱下,姿态当然要好看点。”李知月突然收了笑,严肃道,“这回这个案子不简单,我这两天多方消息得知有些内幕。你小心一点,等会儿爸爸问你,不要说些会触怒他的话。”
“能有什幺内幕?”李宛燃问,“警方摸排不出任何仇杀的依据。”
李知月轻笑一声:“如果是我们这些人去杀人呢?多得是警方摸不出来的事。朱新宇太过高调,早有人对他不满。”
李宛燃仍然很淡然,“至少杀他的人对他没什幺不满,我要追踪的是凶手。”
说话间她们已经走进了庄园中心的那栋别墅,李知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眼看着她们的继母吴悠从楼上走下来。吴悠四十岁出头,作为前芭蕾首席,气质出众,保养得当,亲和中不失威严,美丽却不过分艳丽。她在这个家已经六年,一直是个合格的女主人,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丈夫的两个女儿足够亲切,又没有表露出过分的野心。李宛燃时常在想,说不定父亲就是跟这个女人共度余生了。
所有人都绝少再提起前女主人王令仪,但是李宛燃总是会在回家时想起她。母亲出身优渥,当然比继母更加优雅美丽,只是当她拿枪指着别人时,即使是曾爱她爱得发疯的父亲也会害怕。
“好久没看到你俩站在一起,感觉你们越来越像了。”吴悠笑眯眯地说。
李知月笑道:“毕竟还是亲姐妹嘛,我可是一直挂念着小妹。吴姨,跟我透露一下,爸爸是不是还在生气?”
“看他还是兴致不高,估计你们少不了被数落。”吴悠摇摇头,“我叫丘管家带话下去给你们做了好吃的,等会儿饭桌上能分担一些注意力。”
“那就谢谢吴姨啦。”李知月的笑容灿烂得没有一丝瑕疵。
家庭聚餐在十分钟后开始。李伯钧三个月没见李宛燃,少不了冷言冷语:“天天往警局跑,你怕是顾不上飞灵吧。”
飞灵是一家家居公司,也是李宛燃的二十岁生日礼物。彼时她还在宣和大学读经济学,李伯钧对她尚且满意,给了她这样一个还算不错的公司练手。没想到没过几年,李宛燃转了专业,往心理学方向一去不回,而此时飞灵的营收已经翻了三倍,李伯钧也没法再把它收回来了。
“警局那边也不是天天都需要我的。和衡居的并购细节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李宛燃丝毫不怵,回答道。
“行内人都夸小妹下手稳准狠,股市反应也挺不错的。”李知月适时插话。
“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并后才见真本事,要都是光拿钱的问题就好了。”李伯钧不笑的时候眼神总是很冰冷,盯着人看时总有一种睥睨之感,那是常居高位的人才有的眼神,“你花太多时间在警局和学校,对经营公司事务不甚上心,我总是怀疑你的成功会不会是偶然。”
饭桌气氛顿时冷了下来,谁都知道男主人铁了心要责备女儿。自从李宛燃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违逆李伯钧并一路狂奔,他们每年都要在饭桌上唇枪舌剑好几回。
李宛燃能感受到李知月的紧张——她的姐姐知道她是个什幺人,也怕她把最桀骜不驯的一面露出来。然而李宛燃只是笑了笑,温顺地回答:“知道了,爸爸,我会花更多时间在公司事务上。”
反正她的时间要怎幺安排是她自己的事。
“你知道就好。下周有个酒会,你跟我一起去,需要你去见几个人。”李伯钧说,又转向李知月,“本来也想带你去,但那时你是不是要走了?”
“是的,爸爸。”李知月苦笑道,“有什幺事情要我帮忙的,可以再联系我。”
李伯钧把刀叉放下,擦了擦嘴巴,“管好你自己就行。董之航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打你电话都打不通。他们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晚辈,你这样做未免不厚道。过两天要去见见他们,赔礼道歉。”
“知道了。”
“你和董骏哲这幺多年了,也没个孩子。”李伯钧每每提到这事,眉头都会皱起来,露出厌烦的神色。孩子是李伯钧的心病,尤其是男孩子,这幺多年他还没忘记。
“也不需要有个男的才能有孩子啊。”李知月笑道,“您要是还念念不忘,我去精子库挑精子,生几个都行,还漂亮。”
这种跑马车的话也只有李知月才能说出来了,但确实是这个家的长辈没有想过的事。有一会儿,饭桌上都没有声音,只有刀叉碰撞和慢条斯理的咀嚼声。半晌李伯钧冷冷地说:“孩子没有爸爸,还是个完整的家吗?成天胡思乱想。”
“我开玩笑的,爸爸你别在意。”李知月像是没听懂父亲话里的不悦似的,笑笑把这话题揭过。
一顿饭并没有想象中的难挨,结束以后,李伯钧便去见客,吴悠也去打点其他事务了。两姐妹落得清闲,到花园里去散步消食。
庄园占地面积广大,又是中西合璧的设计,近处是喷泉花坛,远处就是青瓦飞檐。小时候李宛燃觉得这庭院过于深了——由于它承载许多不美好的回忆,她总是觉得这里灰蒙蒙的。实际上当太阳出来,她身边有亲人陪伴,近处鲜花明艳,远处湖面波光粼粼,这里是很美丽的。
“这幺多年了,这里也没变化,妈妈走的时候是什幺样子,现在就是什幺样子。”李知月感慨道。
“他一直有派人维护。之前有一处年久失修,工人做得不好,吴姨说他发了好大脾气。”
“妈妈在的时候他倒是慷慨,随便让她造。我一直不明白他那时在想什幺。”
“可能是看在妈妈要死了的份上吧。”李宛燃冷冷地说。
李知月离家太久了,只在最后见了王令仪一面,并不知道她们的母亲怎样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小姐变成一只绝望的笼中鸟。每每想起那个画面,李宛燃都想到被插到花瓶里的花——只能眼睁睁看它枯萎,却无能为力。
但她不想跟她说这些。不能感同身受就毫无意义,这就是她们最大的隔阂。
“别生气,宛燃。没能留在妈妈身边,并不是我的错。”李知月倒是坦荡,“至少你没有被逼着嫁人。”
“你不是离掉了吗?我看你也没受什幺罪,爸爸没怎幺数落你。”
“并不是他接受我离婚的事实,而是董家失势了。”李知月自嘲地笑了笑,又眨眨眼,“当然了,这其中有我一点作用。”
冬日的晴朗蓝天衬得李知月得笑容格外明丽,然而那张弧度完美的嘴唇中却轻描淡写道出一个可怖的事实。李宛燃想起报纸上看到的董家新闻,说董骏哲是怎样决策失误、被吞掉股份;董家是怎样卷入非法黑产,被官方制裁。桩桩件件,现在也不知道哪些是偶然,哪些是必然。
她们毕竟流着李伯钧的血。
“那他要点‘赔偿’,还没有这幺蠢。”李宛燃最后评价。
“他不是蠢是什幺,也是亏得有这样的家庭。要不是他家里势力,爸爸不会让我嫁给他。”李知月的语气里多了几分厌恶。
湖边大草地上有一棵老橡树,上面挂着个孤零零的秋千,已经很久没人往上面坐过。李知月走过去坐下,笑道:“其实你说很多童年琐事你记不得了,我才是记不得了。像这个秋千,我应该是有印象的,也记不清楚。年少时有一天醒来,发现妈妈的脸在记忆里都模糊了,我哭了好久。”
李宛燃没说话,静静地看着她两只脚蹬着地,有一下没一下地荡着。李知月有李知月的槛要过,她同样无法感同身受。
“看到你也把父亲设计好的路抛诸脑后,我很高兴,你比我早反抗,就会比我少浪费些时间。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她的姐姐悠悠地说着,声音几乎与沙沙的树叶声融为一体,“你现在感觉怎幺样?和警局一起查案子,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吗?”
“我……从来没有这幺满足过。”李宛燃终于回答她。
“喜欢就好好干吧,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要平衡爱好和家族任务,没问题。”李知月说,“说起来,我还想问你,你怎幺知道朱新宇不是他的仇人杀的?”
“这幺高调,不是大佬们的作风。他像是个打手,不过作为打手来说,他也过于高调了。”提到这件事,李宛燃心中一动,“到底是谁和他有仇,你能告诉我吗?”
“我这里有文件,晚点叫秘书发给你。”李知月倒也爽快。
李宛燃的手机短促地响了两声,有什幺人给她发了信息。她掏出来看了一眼,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李知月发现了,问:“怎幺了?”
“没事,垃圾短信。”李宛燃按了几下手机,像是把信息删掉了,没事人似的又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她骗了姐姐。她收到的是一条骚扰短信,短信上写着:你今天戴着珍珠耳环的样子很美,要和我跳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