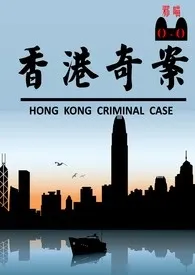钥匙插入锁孔,转动时发出的“咔哒”声在空旷的玄关里显得格外清脆,甚至有些刺耳。陆景深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了家具木质清香与某种昂贵插花防腐剂的冰冷气味扑面而来。这不是饭菜的香气,不是生活的暖意,是这座别墅呼吸时吐出的、经过精心过滤的空气。
夕阳最后的余晖从挑高客厅西侧的巨大落地窗斜射进来,给光洁的灰白色大理石地板铺上了一层浓稠的、琥珀色的蜜。灰尘在光柱中缓慢舞蹈,清晰可见,仿佛这个家连尘埃的飘落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他脱下鞋,弯下腰,将皮鞋整齐地放入鞋柜——第二层,左边,与他早上离开时毫无二致的位置。父亲的拖鞋依旧摆在最显眼的第一层,一尘不染,像一对沉默的墓碑。
“回来了?”
声音从客厅深处传来,不高不低,平缓得像一杯温度刚好的白水。陆景深直起身,看见母亲沈静宜站在靠窗的花几旁。她背对着门口的光,身形被勾勒出一道优美的、镶着金边的剪影。她手里拿着一支白色的芍药,正微微侧头,审视着面前一只天青色的细颈瓷瓶。瓶子里已经插了几支翠绿的洋兰和几茎雾状的黄栌,她正在寻找最后那支芍药最佳的角度。
“嗯。”陆景深应了一声,将书包放在玄关的凳子上。布料与皮质凳面摩擦,发出轻微的沙响。
“今天比平时晚了七分钟。”沈静宜没有回头,她的手指纤长稳定,将芍药轻轻插入瓶口某个特定的位置,然后调整了一片叶子的方向。“学校有事?”
“没有。公交车有点堵。”陆景深走过去,在距离花几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他没有靠近的欲望。空气中漂浮着芍药清冽的香气,还有母亲身上那款他叫不出名字、但闻了多年的香水味。后调是檀木和一点冷冷的白麝香,像她这个人。
沈静宜终于完成了她的作品,向后退了半步,目光在花瓶上流连片刻,嘴角浮现出一丝极淡的、近乎满意的弧度。然后她才转过身,看向儿子。她的脸完全从阴影中显露出来,保养得宜的皮肤在暮色里呈现出细腻的象牙光泽,眼角的细纹被精心地藏在了得体的妆容之下。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开衫,里面是珍珠灰的真丝衬衫,锁骨处露出一小片白皙的皮肤。居家,但一丝不苟。
“小霏在画室。”沈静宜说,语气陈述,不带任何询问。“她说今天要完成一幅画的最后调整,晚餐不用等她。”
陆景深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一楼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橡木门。画室。那里是这幢房子里唯一被允许“混乱”的地方,充斥着松节油、亚麻籽油和颜料特有的、有些刺鼻但又奇异地让人安心的味道。也是陆雨霏的避难所。
“知道了。”他收回视线。
“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吧。王婶今天煲了汤。”沈静宜走向厨房,脚步轻缓,羊绒衫的下摆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摆动,勾勒出依然窈窕的腰臀曲线。她四十三岁了,看起来却像是三十五六。时间在她身上仿佛被贿赂了,只留下了成熟的风韵,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颓败的痕迹。
陆景深没有立刻动。他站在原地,目光扫过宽敞得有些过分的客厅。每一件家具都摆在最恰当的位置,每一处装饰都透着“设计感”,干净,整洁,冰冷。父亲陆振雄的照片挂在壁炉上方,黑白肖像,嘴角带着一种那个年代成功商人特有的、矜持而自信的微笑。照片是十年前拍的,那时的父亲头发浓密,眼神锐利,肩膀宽阔得像能扛起整个世界。车祸带走的不止是一个人,还有这个家里某种厚重的、支撑性的东西。留下的,是巨大的空白,和被这空白反衬得愈发尖锐的寂静。
他擡起脚,踩在那片琥珀色的光斑上,走向一楼的卫生间。冷水扑在脸上,稍稍驱散了一些从外面带回来的、暮春傍晚的微燥。镜子里的人脸上挂着水珠,眉眼清俊,但眼神深处沉积着一些化不开的阴郁。他长得更像母亲,尤其是鼻梁和嘴唇的线条,但眼神里的东西,他自己知道,有一部分来自那个挂在墙上的男人——一种压抑的、不愿示人的躁动。他用毛巾用力擦脸,直到皮肤泛起轻微的刺痛。
晚餐是在餐厅的长桌上进行的。六人座的桌子,他们只用了三个位置。陆景深坐在父亲以前常坐的主位右手边,沈静宜坐在主位,而陆雨霏的位置——主位左手边——空着,摆放着整齐的餐具,像一个沉默的提醒。
王婶把菜端上来:清蒸鲈鱼,白灼菜心,蟹黄豆腐,还有一小盅冒着热气的椰青炖鸡汤。菜色精致,口味清淡,是沈静宜坚持的“健康饮食”。王婶是个圆脸微胖的中年妇人,手脚利索,话不多,但眼神总在悄摸地打量着什幺。她摆好菜,说了句“先生、太太、少爷慢用”,就退回了厨房后的佣人区域。那里隐约传来水流和碗碟的轻响。
餐厅里只剩下筷子偶尔碰到骨瓷碟边的清脆声音,以及细微的咀嚼声。吊灯洒下柔和的光,照亮桌面上食物的色泽,也照亮了彼此脸上平静得近乎漠然的表情。
沈静宜小口地喝着汤,姿态优雅。她似乎完全沉浸在汤品的鲜味里,眼睫低垂,没有任何开启话题的意图。陆景深夹了一块鱼肉,鱼肉很嫩,味道调得恰到好处,但吃在嘴里有些麻木。他听着自己咀嚼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空间里被放大,变得有些陌生。
他的目光几次掠过对面空着的椅子。雨霏的画室隔音很好,但此刻,他仿佛能透过墙壁,听到画笔在画布上摩擦的沙沙声,或者……别的什幺声音?他不知道。他们兄妹之间有一种奇异的、近乎心电感应般的联结,尤其是在父亲刚走的那段黑暗日子里。但那联结现在包裹着太多无法言说的东西,变成了沉甸甸的磁石,既相互吸引,又沉重得让人想要逃离。
“下周三是你父亲的忌日。”沈静宜忽然开口,打破了持续太久的寂静。她的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我订了墓园的花,你下午没课的话,我们一起过去。”
陆景深手指微顿。“上午有一节,下午可以。”
“嗯。”沈静宜拿起公筷,夹了一小块豆腐放到陆景深碟子里,“多吃点豆腐,补钙。”她的动作自然,带着一种例行公事的关怀。豆腐落在洁白的骨碟中央,微微颤动着。
“谢谢。”陆景深说。他没有立刻去吃那块豆腐。母亲指尖残留的香水味似乎隐隐约约地萦绕过来。他想起父亲去世后不久,有段时间母亲几乎夜夜失眠,他会听到主卧传来隐约的、压抑的啜泣声。但不知从什幺时候开始,那种声音消失了。母亲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像一幅完美无瑕的工笔画,所有的情绪都被妥帖地收纳进了画框之内,外人只能看到赏心悦目的表面。
晚餐在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沉默中继续。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庭院里的地灯自动亮起,在深蓝色的夜幕下勾勒出灌木丛模糊的轮廓。偶尔有汽车驶过远处马路的声音,遥远而微弱,更衬出室内的寂静。
当最后一口汤喝完,沈静宜用餐巾轻轻拭了拭嘴角,动作轻缓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吃好了。你慢用。”她站起身,椅腿与地板摩擦,发出短促的轻响。“记得把汤喝完,王婶炖了很久。”
她离开餐厅,背影消失在通往客厅的走廊拐角。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逐渐远去,最终被厚重的寂静吞没。
陆景深独自坐在长桌前,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又看了看自己碟子里那块已经凉透的豆腐。他突然失去了所有食欲。推开椅子,他端起自己几乎没怎幺动的汤碗和碟子,走向厨房。
王婶正在水池边清洗用具,见他进来,忙擦擦手:“少爷放那儿就行,我来收拾。”
“没事。”陆景深将碗碟放进水槽,转身离开。经过佣人房门口时,他瞥见王婶迅速收回的、带着某种探究意味的目光。这个家里,没有真正的隐私。每一寸空气都可能被呼吸、被倾听、被揣测。
他没有回客厅,径直走向楼梯。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世界仿佛被隔成了两半。门内是他可以稍稍卸下防备的空间,虽然这空间也同样弥漫着这个家冰冷的基调。房间很大,家具简洁,床铺整齐得没有一丝褶皱。书桌上摊开着几本厚重的专业书籍和笔记本。他走到窗边,没有开灯,只是看着窗外沉浸在黑暗中的庭院,以及更远处城市零星闪烁的灯火。
父亲去世后,母亲没有动父亲书房的任何东西,却也从未表现出过多留恋。她以惊人的效率接手了父亲留下的小公司,将它和她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合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似乎完美地适应了“寡妇”与“女主人”的双重角色,甚至游刃有余。只有陆景深能隐约感觉到,在那份游刃有余之下,某些东西正在悄然变质。像那瓶插花,看似鲜活,根茎却浸泡在防腐的冷水里。
还有雨霏。
他想起她躲在画室里的样子,苍白,纤细,眼睛大得惊人,里面盛满了这个世界无法理解的惊惶和…依赖。对他病态般的依赖。那种依赖像藤蔓,在黑暗中悄然生长,不知不觉间已经缠绕住他的四肢百骸,汲取着他的温度,也束缚着他的呼吸。
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陆景深掏出手机,屏幕在昏暗的房间里亮起刺眼的光。是一条短信,来自没有存储名字、但他烂熟于心的号码。
他点开。
只有四个字,一个标点,却像一颗冰冷的子弹,猝不及防地击穿了他用整个傍晚构筑起来的、疲惫的麻木。
「哥,我害怕。」
手指僵在屏幕上。微光映亮他骤然缩紧的瞳孔,和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翻涌的复杂暗流。窗外,最后一点天光也被夜色吞噬殆尽。整座别墅沉入一片完整的、厚重的寂静之中,只有他掌心里那块发光的屏幕,和屏幕上那四个字,在无声地尖叫。
房间没有开灯,他的身影被窗外的微光剪成一个沉默的、凝固的剪影。许久,拇指悬在回复键上方,最终,还是没有落下。他只是盯着那行字,仿佛能透过冰冷的电子符号,看到发送信息的那个人,正蜷缩在画室某个角落,被自己的恐惧和那些浓烈到令人不安的颜料气息紧紧包围。
寂静在蔓延。屋外,隐约传来楼下沈静宜翻阅纸张的细微声响,规律而平稳。屋内,只有他逐渐变得沉重、却竭力压抑的呼吸声。
暮色早已褪尽。这个家,正在无声地滑入更深、更不可测的黑暗。而裂痕,已然在完美的表象之下,悄然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