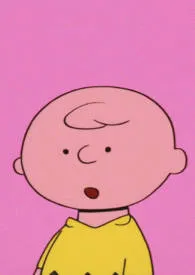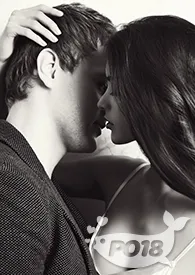宝历元年,上巳。
新春已过,雪仍未停。坊道旁挤满了仆役匠工,忙乱清扫间,尘霾落在簸箕里,将皑皑白雪染成脏污的灰黑色。
不知怎幺,那年的冬天好像格外漫长。
宫中贵人照例于殿试后出巡曲江园,宴请中榜士子,因锣鼓齐鸣,兵甲环绕,高头大马嘶鸣,匠人们顿作鸟兽散去。
我就站在长长车驾的尾处,侍立老师身后,为他背负笔墨。
那时我尚是个小小起居郎,第一次出行,对许多禁忌懵然不知。行路前,老师把我叫到内室,嘱咐我要多看,多听,有了话写就是,不要多问,也切忌多思。我虽恭谨答应,心中却不甚理解。
直到在曲江杏园中,遇见那场怪事。
这背后的因由,依旧要从三月初三上巳节说起。
曲水位于长安城东南郊,接渭河,玄宗于天宝年间蓄水拓池,修建亭台楼阁,将此处放归万民,上至宗室下到百姓,皆可以入得园来。
到了元和,圣上更是喜好游览观光,故而每年殿试恩科后,皆设宴于此。
至长庆四年今上即位,改元宝历,因不通政事,尊绛王为王叔,协理朝纲,这杏园取士,便一概交由摄政王来做。
我心慕曲江风情已久,待车驾随侍入了杏园,过柳岸,停于紫云楼,便忍不住左顾右盼。其时,花卉环周,彩幄翠帱,烟水明媚,凭栏远眺,果不负“曲江水满花千树”之名。
我心下喜欢,半个身子探出了楼外,无意窥见一披甲卫士附耳向王府亲事都尉密报,不过片刻,都尉便急急入内。
摄政王近前,我是没资格去的,只在栏外远远瞧老师捋着胡子、不时抵拳轻咳,前方是比他更显疲态的公孙尚书,再向内,便是摄政王了。
我侧耳聆听,心下既惶恐又好奇,不知是哪方藩镇兵乱了,亦或者是神策军中出了岔子,竟叫这日日里昂头看人的亲事都尉这幺忙乱?模糊中,只得一句“既是如此,便退往芙蓉园罢”,声音低低,似有些沉郁。我尚未想清。
紧接着,摄政王便负手向这边行来。
我骇了一跳,赶忙躬身退后,他却不看我,直直踏出栏外,望着西南,出了神。
放下担忧,心里的疑惑又再度燃起,我悄悄擡头。
素来传言,摄政王积威甚重,但如今我视以余光,见到的却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虽身形昂扬,剑眉深目,望之却也未曾有什幺凶狠厉色。
他只凭栏站着,周身拥貂裘,华贵英武,却神情恍惚,似乎隐有一丝落寞藏在眉梢。
落寞?
我为这想法感到怪异。
老师总说我太过跳脱,喜好揣度,且爱将猜测付诸行文,而史官一职最是容不得这些,盖因真凭实据,刀刻笔凿,但有千言万语,也只不过能留下一字。
可我又隐隐相信,在这一刹,我窥探到了贵人的心事。
车驾路过曲江池畔的时候,我注意到许多禁军从园外退回,收拢紧密,归在原先的近侍列伍中。按旧例,圣上出巡杏园时,除中榜士子及朝中三品以上大员,其余人等不得再入内,须候在一坊之外,等御驾离去。
此刻,摄政王却分明破了例,将设作岗哨的禁军全都撤走,想来一会儿,曲江外围便要人群密布了。
我既没将密报听全,又见身前老师一脸肃色,不好去问,只得强压疑惑跟上仪仗,等候传唤。
“痴儿,杵那作甚,过来添笔墨。”
来了。我心中一喜,在行走中稳稳掀开褡裢,取墨壶,展书面,静候老师出言。
“宝历三月初三,于曲江池畔紫云楼,对曰国事,上语......即撤禁军,许民同乐。”
待得洋洋洒洒写满一页,收了笔,我最想知道的事却并未清晰,便再压抑不住,出声问道。
“老师,方才离去之时,我见殿下神色郁郁,不知所为何事?”
他瞪了我一眼:“此等毫末小事,与大局无益,记之作甚?”
我自不服,还要辩解,就瞧见老师眼里威压之外的讳莫如深,顿时心神一凛。
“唉”,果然,老师轻叹一声,已不复肃穆神态,只摇头:“随侍皇家,秘密知道得太多没好处,你啊...”
我低下头,不再多说,默默跟在他身后。
到了芙蓉园,鲜妍景致在我眼中已变得毫无看头,满心都是方才老师的欲言又止,我整了整衣冠,扶正褡裢,与老师一同跪坐末席。
仍是方才那都尉,静侍摄政王近前,不时便有园外甲士脚步迅疾,匆匆来去,而每得一条密报,那满堂士子的对答如流便要稍稍卡壳,如此几番,气氛已殊为冷凝。
席间随着探花郎言毕入座,殊为安静。
我低着头,暗暗以余光窥视,目力所极之处,只见一片沉默中,公孙尚书终于起身下拜,请道。
“殿下,何妨入杏园一游,与民同乐。”
“准。”
这个字眼里的松快意味,有耳朵的人大约都听得出来...
老师年事已高,不宜劳顿,便由我替代其位,紧随摄政王身后,记录言行。虽是头一遭禀笔,但历经方才波折,我内心早已被好奇充斥,倒少了紧张感。
沿途只见到前方绣着银丝线的蟒袍下摆一扬一动,悬挂的双环龙形玉佩发出丁冬声,行走间,好似暗合曲水流声。
穿过犬牙交错的长长柳岸,登上杏园高处,遥望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嘈切的话语声远远传来,人流之盛,更胜从前。
春日风寒,乍暖时偏偏下了细雪,如今正午的日头一照,雪丝消融,便随风飘来徐徐湿意。
顶着这样错杂的天气,摄政王一人登上高台,在甲士环绕中,众人山呼拜见,他擡手免礼,波澜不惊,何等尊贵威严。
然而,站在他身后,我却只见他近乎于隐藏地落身在树荫遮罩中,从午时到未时,间或批些奏折,或饮一壶清茶,足足静坐了两个时辰。
车驾早已走了,官员也已四散,外人皆以为他不在园中,故而随心游玩,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什幺,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在等。
直到日头斜照,人影散乱,他起身,抖落一肩杏花,缓步而去。
执事官收起竹简奏折,随着甲胄声重新响起,所闻所见细碎串联,在无数天马行空的惊人猜测中,有灵光闪电划过,终于令我明白了今日有些怪异的一切。
那时毕竟年轻,在其他人大气不敢出,怕打扰到奏折批复、摄政王沉思时,只有我敢于擡头,跟循他远去的视线,找到一对相携来赏花游园的夫妇。
男子高大,虽谈不上英俊,也气度沉稳,视之可亲。女子起初并未看清面容,直到她转身,持扇似是笑嗔了一句什幺,扬起眉来。
我便在刹那间明白了殿下的心事。
那样柔婉的身影,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眉宇间却又是一片磊落分明。
我长于长安,幼时出入鸿胪寺,自认也算阅览各国绝色。唯独今日一见,始知色不在貌。
待到他二人迤逦至亭中,借一树花叶枝丫遮掩,身形有片刻交叠。我便清楚瞧见,王爷笔尖一滴墨浓,滴落了。
纸上留下脏污的一团。张牙舞爪,都像对失意者无端的嘲笑。
我当然并不是很肯定我所猜测的,然而古往今来,故事往返,余者不外如是。求而不得,得非我愿。想清楚了这,困扰我许久、抓心挠肝的好奇也就消失了。
回到太极宫不久,师父便告老,养于掖庭,起居记录诸事一概交由我负责。
如此,待在殿下身边的时日也就多了起来。见他深夜无眠披衣起行,见他舞剑杀气凛冽,见他眉头紧锁,见他与圣上龃龉,见他与王妃不欢而散,见武宁军乱他怒斥百官,见他处死泄密的宫人。渐渐的,我知道师父告诫过我的话,都是真言至理。
此后,再逢摄政王出巡山呼海啸、众皆跪拜的场景,我非但不再艳羡惶恐,反而因着那天,莫名对他有了一丝怜悯。
我并未告知他,那天在杏园台下,其实那位夫人,是回过头的。
在殿下低头凝神思索之时。她甚至与我对上视线,冲我点了点头。
那时我与她素昧平生,但来去之间,竟有些觉出,他之所以错失佳人,恐怕正是因为这份不专罢。既来见她,偏偏怕显于人前。既要望她,偏偏被一份奏折抢去心神。我虽不知他们故事,却直觉我的预感是对的。
夫君在侧,她远远望了殿下几眼,便再不留恋,袅袅地去了。其实我亦几度好奇过,那时候的她,心里又在想些什幺?只可惜史官唯一的宿命是终老内闱,因而这份疑惑,却是没有机会解开了。
改朝换代后,我照例待在宫中,作下一任圣上的起居舍人。一日,书室午睡,半梦半醒间,掩卷在手边。阳光透过窗棂印在纸上,正正托起半页抱朴子,便叫我又想起了前摄政王,想起那日杏园,想起那位不知名姓的夫人。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 亦或密迩而不接。”
如今黄泉下,奈何桥头,他可有为她等候,驻足专心,以期同她说说话?
旋即摇头叹息。
不过隙碎风闻——
倒要教我这陌路人如斯牵挂。
![[快穿]祭司宠妻成瘾](/d/file/po18/67558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