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次,天下英才尽入京华——
杏花微雨,春闱开考。
大端的春闱素来隆重,三年一次,四方学子齐聚玉京,寒窗苦读数载,皆为这场科举。贡院之外,人潮涌动,文士青衿,皆是意气风发。
我立于太学院藏书楼高台,望着贡院门前长街上扶案誊写的考生。
贡院巍峨如巨兽蛰伏,九重朱门次第洞开,青石阶上雨痕斑驳,似泼墨长卷。
考生们鱼贯而入,或紧攥考篮指节发白,或昂首阔步睥睨众生。有人衣襟补丁却脊背挺直,有人锦袍玉带却神色惶然。
檐角铜铃轻响,细雨濡湿了“为国求贤”的金匾。
春雷初动,细雨如酥。
太学南苑的杏花林里,我独坐石亭,面前摊着一卷《水经注》。
忽有杏花落于砚台,溅起一滴墨,污了书页。
宋卷执伞踏雨而至,杏花簌簌落于伞面。
他垂眸看向案上被墨迹污损的《水经注》,指尖在“洛水”二字上轻轻一叩:“殿下冒雨来太学查河道旧档,是为春闱策论题?”
我暂未答,只将染墨的杏花拈起,花瓣上的雨珠滚落砚台,晕开一圈涟漪:“你冒雨踏泥而来,总不会是为同本宫赏花。”
他忽然轻笑,笑意未达眼底,广袖一展,将一卷泛黄舆图铺在案上。图上赫然是玉京七十二渠的水道脉络,其中洛水支流处密密麻麻批注着小楷,字迹凌厉如刀削——正是三年前工部呈报的《疏河纪要》。
“三日前,陛下命太师府协理春闱出题。”他指尖点在图上一处溃堤标记,“策论题‘治河如治国’,是臣拟的。”
我凝视着舆图上那道溃口,记起三年前洛水决堤,浮尸塞川的惨状历历在目。
“好一个‘治河如治国’。”我擡眸冷笑,“这是要学子们论‘堵’还是论‘疏’?”
他指尖在舆图上轻轻划过,沿着洛水支流的脉络一路向下,最终停在一处标注为“淤积”的位置:“堵与疏,不过表象。真正的症结在于人心。”
他擡眸看我,目光如深潭般沉静,“殿下以为呢?”
我起身,将《水经注》合上,淡淡道:“这策论题,本宫准了。”
宋卷躬身一礼:“殿下英明。”
石亭外雨势渐急,杏花簌簌落雨,贡院内的铜锣声穿透雨幕,惊起林间栖鸟。
三日后,杏花落尽,春闱落幕。
贡院门前,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檐角铜铃在风中轻响,似在催促蛰伏的万物破土而出。
晨曦初露,远处钟鼓齐鸣——巳时三刻,贡院放榜。
人潮如织,挤满了贡院前的长街。
贡院朱门缓缓开启,一队礼官手捧金榜,步履庄重地走向高悬的揭榜处。
金榜高悬,红绸覆盖。
“放榜——”礼官高唱,声如洪钟。
红绸缓缓揭开,金漆榜文在春日下熠熠生辉。
“头甲贡士——江州顾星辰!”
唱名声落,满街寂静了一瞬。
“顾星辰?从未听过此人!”
“江州寒门……”
人群炸开喧嚣,有人惊愕,有人愤懑,更有人踉跄后退,撞翻了街边卖栀子花的竹篓,素白花瓣与泥水混作一团。
远处忽起骚动。几名锦袍公子围住顾星辰,为首者正是谢侍郎家的嫡孙谢昀。
他手中折扇抵在顾星辰肩头,玉坠穗子随冷笑晃动:“寒门竖子也配?怕是连你江州老家的田契,都是偷了哪位大人的墨宝换来的吧?”
顾星辰后退半步,他拱手一礼,声音清朗如初春融冰:“谢公子若疑学生舞弊,可按律呈递都察院。”
“你!”谢昀的折扇猛然扬起——
“放肆!”
一声冷喝穿透喧嚣。
金甲禁军,马蹄踏碎满地栀子花。
赵昭端坐马上,剑鞘横在谢昀腕间:“贡院门前辱及新进贡士,按律当杖三十。”
贡院对面茶楼二层,茜纱窗后。
少女斜倚凭栏,素手捏着青瓷茶盏,指尖在盏沿轻轻一叩。
“殿下,要召他入宫谢恩幺?”阿萦低声问。
“急什幺?雏凤初啼,总得让朝中那些老狐狸听听这清音。”我轻笑,轻轻吹散茶香。
窗外忽有风过,檐角铜铃轻响,与贡院前的声响混作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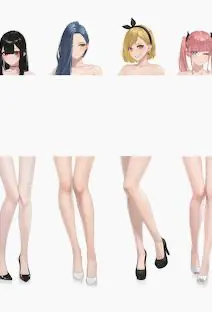




![缅铃[沙雕女主混官场]](/d/file/po18/710974.webp)



![[电竞nph]我要的是荣耀](/d/file/po18/82335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