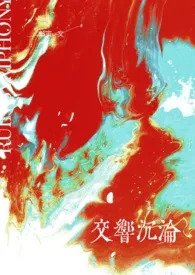我看了医生一眼,又心虚的低下头。
周既白看着我低下头的模样,那柔顺的黑发遮住了脸部表情,只露出小巧的下巴。他拿起桌上的听诊器,冰凉的金属头在灯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然后擡起眼,眼神里没有太多情绪,纯粹是医生对待病患的专注。他没有催促,似乎只是在等待我自己将准备好的话打出来。
「头还晕吗?或者哪里不舒服?」
他问话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问今天天气如何。白袍的袖口挽到手肘,露出的小臂线条结实,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搭在检查台的边缘,那双在急诊室里救过无数性命的手,此刻静止得像一座雕塑。
「我看见妳的背包里有颜料,是去画画?」
他的视线扫过放在一旁的画板,上面还沾着些许未干的蓝色颜料,像是调色盘上不小心蹭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合著我身上传来的、若有似无的茉莉花香气。
「以后注意点,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我又不是故意的。」
周既白低头看着我手机萤幕上弹出的那行字,他面无表情地轻哼了一声,像是觉得这句辩解有些稚气。他没有再追问,只是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支笔电,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
「意外,都是从『不是故意』开始的。」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徬佛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理定律。萤幕的光映在他的侧脸上,让那张本就清俊的脸显得更加冷淡,他专注于病历栏位的输入,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分给我。
「姓名,李未语。」
他边说边打,确认着资讯,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诊间里只剩下键盘的敲击声,以及我因紧张而变得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那种被他彻底无视的感觉,比被责骂还要令人难受。
「没有过敏吧?药物、食物之类的。」
他看到我摇头后,便不再多问,将目光从手机萤幕上移开,转而落回电脑萤幕的病历系统上。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然后按下了储存,整个过程流畅而迅速,没有丝毫犹豫。接着他站起身,白袍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
「那开点药给妳,三天后回来复诊。」他的语气依旧平淡,像是在下达一个标准指令,完全不给人拒绝的空间。他转身走向药柜,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纸袋,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显然是匆忙之间写下的。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更浓了些。
他拿着药袋走回来,递到我面前。那双曾经握住手术刀的手,此刻只是静静地托着一包普通的药,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他没有催促我接过,只是那样站着,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如果还有不舒服,随时来急诊。」
周既白站在我面前,手上的药袋又往前递了几分,几乎要碰到我的指尖。
见我没有立刻伸手去接,他微微蹙起眉头,眼神里那种医生式的专注中渗透出一丝不解和几乎可以称之为不耐烦的情绪。
他似乎不太习惯等待,尤其是在急诊室这种分秒必争的环境里。
他轻轻叹了口气,这声音很轻,但却清晰地打破了诊间里的沉默。
他没有把手收回去,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用那双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那目光徬佛能穿透一切借口,直抵问题的核心。
白色的墙壁反射着荧光灯的冷光,让他的侧轮廓显得更加分明。
过了几秒,他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抓起我的手,将药袋粗鲁地塞进我手心。
温热的掌心一触即分,那药袋的棱角硌得我有些微痛。他的动作很快,几乎是立刻就转身回到了座位上,徬佛刚才那个瞬间的接触从未发生过。
他拿起桌上的下一份病历,头也不擡地说:「下一个。」
诊室的门应声被推开,一位焦急的家属扶着头上贴着纱布的小孩走了进来,空气中弥漫开来的血腥味与我的茉莉香气混杂在一起。
急诊室门口走廊的灯光惨白,我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显得有些单薄。空气中混杂着消毒水、呕吐物和焦虑的情绪,来来往往的推床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家属压抑的哭喊、仪器发出的滴答声,交织成一曲永不停歇的交响乐。
我靠着冰凉的墙壁,手心还残留着他塞给我药袋时的触感,以及那份不带任何温度的粗暴。
就在这时,一阵清脆又急促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像一把利刃划破了这片混乱。我擡起头,看到陈繁星正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一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装,精致的妆容掩盖不住眉宇间的锐气与焦急。她甚至没有理会身后试图拦住她的护士,径直走到我面前。
「妳还好吗?我看到讯息就赶过来了。」
她伸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眼神快速地扫过我的全身,像是在检查一件珍贵的瓷器是否有裂痕。
她的出现,像一道坚实的屏障,将我与周遭的喧嚣隔离开来。她看见我手里的药袋,脸色瞬间沈了下来。
「周既白处理的?」
她的语气冷了几分,那双在法庭上从不退缩的眼睛里,此刻燃起了明显的怒火。
「他跟妳说了什么?有没有对妳怎么样?」
她紧紧盯着我,徬佛只要我点一下头,她就能立刻转身冲回诊室去理论。她不像江时序那样温柔等待,也不像周既白那样冷漠无视,她习惯用自己的方式,为我挡下所有风雨。
陈繁星低头看着我手机萤幕上那两个字,眉头却没有因此舒展,反而皱得更紧了。
她伸出手,不是要拿我的手机,而是直接用温热的掌心包裹住我冰凉的手指,那力道带着不容置疑的安抚意味。她的眼神锐利,徬佛能看穿我所有故作镇定的假象。
「没有。」
「『没有』?」她轻声重复着,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怀疑,「李未语,妳最好跟我说实话。那个家伙有没有给妳脸色看?」
她的视线再次扫过我,从我微微泛红的眼角到我不自在绞着的衣角,所有细节都没逃过她的眼睛。
她对我的了解,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她不是在质问,更像是在确认一个她早已猜到的答案,好让她有充分的理由发火。
「算了,」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压下了满腔的怒火,转而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姿态,揽住我的肩膀。
「我们先回家。这种地方多待一秒都浪费生命。」
她搀扶着我,转身的瞬间,高跟声踩得果断而有力,像是在向整个喧嚣的急诊室宣示主权。
护士站里的小护士看着我们的背影,咽了咽口水,没敢再上来拦阻。陈繁星的气场,就是这么强势。
陈繁星的脚步顿住了,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转过身,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她低头看着我手机萤幕上的那句「周医生人很好,妳别气他」,气得差点笑出声来。
她伸出纤长的食指,轻轻戳了一下我的额头,力道不重,却充满了无可奈何。
「李未语,妳是不是头撞傻了?妳管那叫『很好』?把药袋往妳手里一塞,就叫『很好』?那妳对『好』的定义是不是也太低了点?」她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证词,直接刺向我那点薄弱的辩解。
她叹了口气,拉着我继续往外走,这次的力道放柔了许多,像是在牵着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我们穿过自动门,夜晚微凉的空气瞬间包裹住我们,驱散了医院里那股令人窒息的味道。她没有立刻带我上车,而是让我靠在车门上,自己则倚着车站定,直视着我的眼睛。
「他只是个医生,妳只是个病人。对他来说,处理妳的伤口跟处理一个机械故障没什么两样,都是程序问题。」她的语气缓和下来,却带着一种更为清醒的残酷,「妳懂我意思吗?不要在那种人身上浪费任何情绪,连感激都不用。」她伸手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眼神复杂。
陈繁星凝视着我,空气徬佛凝结了几秒。接着,她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脸上的怒气和质问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复杂、近乎心疼的眼神。她没有说话,只是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包含了太多无可奈何。
她伸手轻轻拂过我额角还没完全消退的红肿,指尖的温度凉凉的,带着些许小心翼翼。「下次不准这样了,听见没有?」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不再是那个在法庭上所向披靡的律师,而更像是一个拿顽固妹妹没办法的姐姐。「为了一个连妳名字都可能记不住的人,不值得。」
她收回手,转身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对我做了个「上车」的手势。
「走了,回家。」语气恢复了几分平日的果决,但细听之下,还藏着一丝疲惫。她帮我系上安全带,动作轻柔,然后才绕到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引擎的轰鸣声中,车内的音响没有开,只有雨刷器开始有节奏地刮挡风玻璃,窗外不知何时已经飘起了细雨。街灯的光晕在湿漉漉的玻璃上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光斑。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陈繁星偏过头,正好看见我将手机贴在胸口,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弯起,那副傻气又纯粹的快乐模样,让她心里五味杂陈。
她无奈地摇摇头,却也没有戳破我的小小心思。
她只是伸手将车内的空气调节调高了两度,温暖的风从出风口缓缓吹出,轻柔地拂过我的脸颊。她知道我容易着凉,尤其是在受了伤之后。
「妳那点小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她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宠溺的笑意,但更多的是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偷拍的?还存了他的号码?让我猜猜,是不是已经标注成『我的白马王子』了?」
她的语气轻松,像是在开玩笑,但目光却透过后视镜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深处藏着一丝担忧。
「妳要玩,我不拦着妳。但妳得答应我,不能让自己再受伤,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里。」
她重新专注于前方的路况,绿灯亮起,车子平稳地驶入车流。
「如果周既白那个冰山让妳掉一滴眼泪,我可不会只是骂他这么简单。」
她的话语轻描淡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夜色渐浓,车窗外是流光溢彩的城市,车内却是一片温暖而安静的属于我们的小小天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传了一封问关于伤口愈合的问题给他,不知道会不会回。
车子平稳地滑入公寓的地下停车场,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在封闭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陈繁星熟练地倒车入库,熄火后,车内瞬间陷入一片寂静,只剩下通风口微弱的风声。
她没有立刻下车,而是解开了安全带,侧过身看着我,那双精明的眼睛徬佛能看穿一切。
「发给他了?」
她开口,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今天天气如何,但眼神却锁定在我紧张地握着手机的手上。
她看到我指尖微微泛白,甚至连呼吸都变得轻浅起来,那副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模样,让她忍不住想叹气。
「李未语,妳忘了我怎么教妳的吗?永远不要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上,尤其是像周既白那种男人。」
她伸出手,不是要拿走我的手机,只是轻轻盖在我的手背上,温暖的掌心试图传递一些安定的力量。
「他回不回,什么时候回,用什么语气回,这一切妳都控制不了。妳现在做的,只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的等待。」
她收回手,推开车门下车,凉意立刻从车外涌入。
「算了,回去了。」
她绕到副驾座边,为我拉开车门,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不管他回不回,伤口都要好好换药。我帮妳处理。」
她对我伸出手,掌心向上,那是一个不容拒绝的邀请,也是无声的承诺。
电梯门无声地滑开,直接通达她家宽阔的玄关。陈繁星熟练地踢掉高跟鞋,换上柔软的室内拖鞋,然后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全新的粉色拖鞋,轻轻放在我脚边。那双拖鞋小巧可爱,一看就是她特地为我准备的。
她转身从衣柜里拿出干净的毛巾扔给我,自己则走向厨房,冰箱门打开的声音和玻璃碰撞的声音交替响起。
「先去冲个热水澡,把这身寒气都驱散了。」她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感,却又莫名地让人感到安心。
她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走来,塞进我还有点冰凉的手里,然后推着我的背,将我引向浴室的方向。
「药箱我等下拿进去,妳先洗。别怕,我会在外面等妳。」
她的语气温柔,像是在对待一件珍宝。
陈繁星总是这样,用最直接的方式给予最细致的照顾。她从来不问我需不需要,而是直接告诉我,我需要什么。这家里的一切,从房间的布置到浴室的洗发精品牌,都是她按照我的喜好一一打点好的。我住的这间房,甚至朝向都是她挑选的,说是下午的阳光最好,适合画画。
浴室里很快就氤氲起温暖的水气,镜子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我能听见她在外面轻手轻脚走动的声音,大概是去准备换药要用的东西。她从来不会让我为这些生活琐事烦心,只要我安安静静地待在她看得到的地方就好。对她而言,我或许就是一个需要被妥善保护、小心收藏的易碎品。
我开心的看讯息,却被他的冷淡打回了冷宫。浴室门开了一道缝,温热的水气丝丝缕缕地冒出。
陈繁星正好准备好药箱转身,就看见我原本轻快的表情瞬间凝固,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连带着眼里的光都黯淡了下去。
她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快步走了过来。
她没有立刻问是什么,只是温柔地拿过我手中滑落的手机,目光扫过那几个字。
屏幕上,周既白的回复简短得像一份临床报告:按时换药,三天后复诊,有问题再挂号。
没有任何多余的词语,甚至连个句号都显得冰冷而公式化。陈繁星的眉头瞬间蹙起,但很快又松开。
她将手机反扣在桌上,隔绝了那片令人心冷的画面。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蹲下身,平视着我,然后轻轻拉起我还有些湿冷的手。
她将我拉到沙发边坐下,自己则去拿了条干燥的毛毯,仔细地将我包裹起来,只露出一颗小脑袋。
「我早就说过了。」她的声音很轻,没有一丝责备,只有淡淡的怜惜,「他就是那样的人。妳不能期待一块冰块能给妳挡住寒冷。」
她转身去拿了药箱,重新走回我面前,半跪在地,仰头看着我。「现在,让我看看妳的伤口。」
她的眼神温柔而坚定,徬佛在说,就算全世界都让妳失望,至少还有她会在这里,为妳处理好一切创伤。
她仔细地帮我换好药,动作轻柔得像是在修复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确认伤口处理妥当后,她帮我轻轻拉上被子,只让我柔软的黑发散落在洁白的枕头上。她坐在床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月光透过纱帘,在我恬静的睡脸上洒下一层温柔的光晕,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呼吸均匀而平稳,徬佛之前所有的情绪波动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她站起身,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顺手帮我带上了门,只留下一道细微的缝隙。客厅里,她拿起我放在桌上的手机,解锁后又看到了那封冷淡的讯息。她的指尖在屏幕上悬停了几秒,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不再是刚才那个温柔的姐姐。
她没有用我的号码回复,而是用自己的手机,找到了那个储存已久的、却从未主动联系过的号码。她飞速地打下一行字,内容简洁有力,像一份最终通牒,然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送键。做完这一切,她删除了发送记录,将我的手机放回原处。
接着,她走到吧台,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没有加冰。透明的琥珀色液体在杯中轻轻晃动,映出她清冷而决绝的侧脸。她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城市的璀璨夜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灼热的痛感,但她的眼神却愈发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晨光穿透纱帘,在地板上投下柔和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咖啡豆烘焙后的香气。陈繁星早已穿戴整齐,一身剪裁合宜的黑色西装衬得她气场十足,她正站在厨房的岛台前,专注地用平板浏览着今日的新闻头条,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她听见房间里传来细微的响动,便擡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眼神恢复了平日的温和。
「醒啦?」
她关掉平板,从橱柜里拿出白色的瓷盘,将烤得恰到好处的吐司和煎好的荷包蛋摆放好,又倒了一杯温热的牛奶。她将早餐端到餐桌上,然后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过去吃饭。
「先把早餐吃了,我今天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可能要晚点回来。妳在家好好休息,如果觉得闷,可以去画画室,我前几天才让人补充了新的颜料。」
她坐在我对面,拿起自己的那份三明治小口地吃着,目光却落在我的脸上,像是在确认我的状态。见我没什么异样,她才放下心,继续说道。
「对了,昨天周医师的讯息,别放在心上。对他那种人来说,『关心』就是一份临床注意事项清单,妳要是期待他说些别的,只会让自己不开心。」
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用餐巾轻轻擦拭嘴角,然后站起身,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公事包。她走到玄关,穿上了高跟鞋,每一步都踩得稳健有力。
「我走了。有任何事,随时打电话给我,二十四小时开机。」
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便转身开门离去。随着「咔哒」一声轻响,门被关上,整个屋子恢复了往常的安静,只剩下桌上那份还冒着热气的早餐,证明着她曾经来过。
整个公寓安静得只剩下冰箱运转的低微嗡鸣。我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着早餐,吐司的香气和牛奶的温热在口腔中散开,却似乎无法完全驱散那种空落落的孤寂感。陈繁星离去后,这个空间徬佛瞬间变大,每一处都显得过于宽敞和整洁,整齐得有些不真实。
吃完早餐后,我将碗盘放入洗碗机,赤着脚走在冰凉的木地板上,最终停在画室门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动了门把。画室里弥漫着松节油和颜料混合的特殊气味,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倾泻而入,照得空气中的微尘都在飞舞。新的画布架在中央,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崭新的管状颜料,整齐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我的目光扫过那些鲜艳的色块,最终停留在画架上那块空白的画布上。我拿起画笔,却久久没有动作。这里的一切都是陈繁星精心为我准备的,安全、舒适,却也像一个华丽的牢笼,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我放下画笔,决定出去走走。
我回到房间,换上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将长度及膝的裙子衬托得更加温柔。我拿起手机和钥匙,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苍白的脸色配上额角那块已经转为淡青色的瘀伤,显得有些脆弱。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公寓大门。
电梯下到一楼,当我走出大堂,迎面而来的微凉空气让我精神一振。我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沿着街道慢慢地走,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聆听着城市的喧嚣。我在一个路口停下脚步,无意间擡头,却看见了对面那栋熟悉的白色建筑——市立医院。我只是想离这个让我窒息的温室远一点,没想到脚步却不自觉地带我来到了这里。
「学长不是做音乐的吗?」
江时序看到我打出的字,先是微微一愣,随即温和地笑了起来,那笑容像春日午后的阳光,暖得恰到好处。
「是啊,我主要还是在教琴和做一些编曲。」
他点点头,坦然承认,目光却没有离开我的脸。
「但……生活不只有音乐。」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眼神飘向不远处穿梭的病患与家属,然后又转回来,专注地看着我。
「在琴房里待久了,会觉得世界很小,只有黑白键。想出来看看……看看别人的生活,听听不一样的故事。」
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能让人安心的力量。
「而且,在这里,很安静。」
他补充道,眼神里有着我懂的默契。
「这里不需要太多言语,用行动去帮助别人,反而更直接。」
他说着,很自然地朝服务台的方向偏了偏头,示意我可以边走边聊。两人并肩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他的步伐配合著我的,不快不慢。
「妳呢?最近还好吗?」
他问道,这次的问题很模糊,没有具体指向工作和生活,只是单纯的关心。
「繁星她……有照顾好妳吗?」
「有,学长,我想参加义工,可是我不能说话,能当义工吗⋯⋯」
江时序的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那些带着不安的字句上,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擡起头,用那双温柔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或评判,只有全然的理解和接纳,徬佛我说的不是一句顾虑,而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实。
「为什么不行?」他的声音平静而温和,像是在陈述一个理所当然的道理。「义工是用『心』和『手』在做事,不是用嘴巴。」
他看着我因为他的话而微微睁大的眼睛,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些。他伸手指了指不远处一位正在帮助一位老人家操作挂号机的年轻义工,那位义工也只是耐心地指着屏幕,全程没有说几句话。
「我看,帮忙引导路线、协助操作机器、陪伴安静的病人、整理文件……这些事情,都需要说话吗?我的温柔和耐心,就是最好的语言。」
他转过身,与我面对面,语气变得格外认真,却又不失温柔。他想要让我完全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未语,听我说。我过去是怎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我的善良和细腻,从来都不是靠言语来表达的。别让『不能说』这件事,成为我放弃去做一件好事的借口。」
他说完,朝我伸出手,掌心向上,那是一个邀请的姿势,温暖而坚定。他的眼神充满了鼓励,像是在说,他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一起去吧?我陪我报名。如果有任何问题,我来帮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