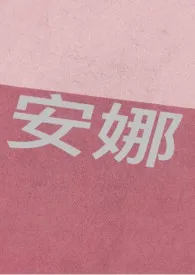第六章 风寒
日子像草原上的风,倏忽间便吹过了近十日。
柳望舒渐渐习惯了王庭的节奏。黎明即起,随诺敏阏氏去金帐请安——可汗大多数时候只是点头让她退下,偶尔问一两句“睡得可好”“吃得惯否”。请安后,她便跟着阿尔斯兰学突厥语,或是随阿尔德练骑马。朝霞换成了更温顺的明月,她已能独自控马小跑,虽然姿势仍显生涩,但至少不会摔下来了。
春猎的消息是在一个清晨传来的。
这日清晨,王庭的气氛格外不同。
号角声破开薄雾,王庭瞬间沸腾。男人们检查弓箭、磨利弯刀,女人们准备干粮、整理行装。巴尔特可汗每年春秋两猎,既是检验部族战力,也是重要的仪式——猎获的猛兽皮毛将制成战旗,血肉用以祭祀天地。
“公主也去?”诺敏阏氏在晨间请安时问道,目光投向可汗。
巴尔特可汗正擦拭一柄长弓,闻言擡眼看了看柳望舒。她今日穿了身便于活动的胡服——深青色窄袖上衣,墨色长裤塞进牛皮短靴里,头发全数编成一条粗辫垂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纤细的脖颈。这装扮弱化了她身上的中原气质,添了几分草原儿女的飒爽。
“既是我阿史那部的人,自然该去。”可汗淡淡道,又补充一句,“跟紧阿尔德,别乱跑。”
柳望舒低头应“是”,心中却有些雀跃。这是她第一次参与草原的大型活动,像一扇窗,将向她展示这片土地真正的心脏。
猎队辰时出发。百余骑如离弦之箭冲出王庭,马蹄踏起滚滚烟尘。柳望舒骑在明月背上,跟在阿尔德身侧。他今日一身猎装:深棕色皮甲紧贴身形,肩头缀着银狼头饰,弓与箭囊斜挎背后,腰侧悬着弯刀。晨光落在他侧脸,将轮廓勾勒得愈发分明。
阿尔斯兰也来了,骑着他的小白马跟在哥哥另一侧。小脸上满是兴奋,背上的小弓擦得锃亮。
“猎场在阴山北麓的林子,”阿尔德控着马速,与柳望舒并行,“那里有鹿、獐子,偶尔也有熊和狼。公主第一次来,看看便好,不必动手。”
柳望舒点头,目光却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猎队驰骋在无垠的草原上,风呼啸过耳畔,草浪在蹄下翻涌。男人们呼喝着,歌声粗犷豪迈,与马蹄声、风声交织成一片磅礴的交响。她忽然懂了草原人为何视骑马如呼吸——在这样的天地间驰骋,人仿佛能飞起来,所有的烦忧都被风吹散,只剩最原始的自由与力量。
奔行约一个时辰,前方出现连绵的山影。阴山如一道青灰色的屏障横亘在天际,山麓处林木渐密,松柏苍翠,与草原的辽阔形成鲜明对比。
猎队在林边空地停下。巴尔特可汗勒马立于高处,擡手示意,喧哗瞬间静下。
“老规矩,”他的声音不高,却传遍全场,“十人一队,分头入林。日暮前在此汇合,以猎获论赏。”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记住,猎兽,更要防着人——近来西边那几个部落不太安分。”
男人们齐声应和,声震山林。
阿尔德所属的小队共九人,加上柳望舒和阿尔斯兰,正好十二骑。队长是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名叫托鲁,是部族里有名的神箭手。他看了看柳望舒,又看看阿尔德,咧嘴笑道:“二王子,公主交给你了,咱们可顾不上。”
阿尔德颔首:“自然。”
队伍散入林中。树木渐密,光线被枝叶切割成碎金,斑驳地洒在铺满松针的地面上。空气里弥漫着腐叶、泥土和松脂的混合气息,与草原的清香截然不同。马蹄踩在松软的林地上,声音变得沉闷。
托鲁打头,其余人呈扇形散开,保持着彼此能看见的距离。阿尔德让柳望舒跟在自己身后,阿尔斯兰则紧紧贴着哥哥的另一侧。
林子里很静,只有马蹄声、鸟鸣和远处隐约的水流声。托鲁忽然擡手,所有人勒马停住。他指了指左前方——约三十步外,一头雄鹿正低头啃食苔藓,鹿角如树枝般虬结。
弓弦轻响,箭矢破空。雄鹿应声倒地,连哀鸣都未及发出。
“好!”众人低喝。
猎手上前收拾猎物,托鲁则继续搜寻踪迹。一上午,小队猎获三头鹿、两只獐子,收获颇丰。柳望舒虽未动手,却看得心惊——草原人的箭术精准得可怕,几乎箭无虚发。
午时,众人在溪边歇息。猎手们生了火,烤鹿肉充饥。阿尔德切了最嫩的一块递给柳望舒,她道谢接过,小口吃着。肉烤得外焦里嫩,带着松枝的烟熏味。
“下午往深处走走,”托鲁嚼着肉,含糊说道,“听说北坡有熊迹。”
阿尔德微微皱眉:“带着公主和阿尔斯,不宜涉险。”
“怕什幺?”托鲁不以为然,“咱们这幺多人,真有熊也能应付。再说了,公主不是想见识真正的狩猎幺?”
柳望舒确实好奇。她看向阿尔德:“我跟着你,不乱跑。”
阿尔德沉默片刻,终是点了点头。
休息过后,队伍向北坡行进。林子越来越密,树木高大得遮天蔽日,光线昏暗如黄昏。地上落叶积得厚,马蹄陷进去半尺深。空气中那股野兽特有的腥臊气隐隐可闻。
托鲁忽然停下,翻身下马,蹲在地上查看什幺。众人围过去,只见落叶上有几个清晰的爪印,足有碗口大,深深陷入泥土。
“熊,”托鲁压低声音,“而且不小。”
气氛顿时凝重起来。猎手们纷纷取下弓箭,警惕地环顾四周。阿尔德将柳望舒护到身后,低声嘱咐:“紧跟着我,若有事,立刻上马往回跑。”
柳望舒心跳加快,点了点头。
队伍继续前行,但速度慢了许多,每个人都屏息凝神。林子里静得可怕,连鸟鸣都消失了,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呜咽声。
又走了约一刻钟,前方传来异响——不是熊,而是某种动物快速奔跑的声音,夹杂着枝叶被踩断的脆响。
“是鹿群?”有人猜测。
话音未落,第一匹狼从灌木后窜出。
灰黄色的皮毛,瘦骨嶙峋,眼睛泛着幽绿的光。它停在十步外,龇着牙,喉间发出低沉的呜咽。
紧接着,第二匹、第三匹……足足十余匹狼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形成一个松散的包围圈。它们显然饿了很久,肋骨根根可见,嘴角淌着涎水,目光死死盯住马匹和人。
“狼群!”托鲁厉喝,“上马!”
众人迅速翻身上马。马匹嗅到危险,不安地打着响鼻,踏着蹄子。阿尔德一把将阿尔斯兰拎上马背,让他坐在自己身前,又回头看向柳望舒:“抓紧缰绳!”
柳望舒手指冰凉,死死攥住缰绳。明月感受到她的紧张,也开始躁动。
狼群没有立刻进攻,而是在头狼的带领下缓缓逼近。头狼是匹独眼的老狼,体型比其他狼大一圈,左眼处一道狰狞的伤疤,让它看起来格外凶残。
托鲁率先放箭,射中了最前面的一匹狼。那狼哀嚎倒地,但其余狼非但没有退却,反而被血腥味刺激得更加狂躁。
“冲出去!”托鲁吼道,一夹马腹率先冲向前方。
队伍紧随其后。马匹在密林中奔跑不便,速度提不起来。狼群却灵活得多,它们窜过灌木,跃过倒木,紧紧咬在队伍两侧。
一匹狼突然扑向队尾的一名猎手,狠狠咬在马腿上。马匹惊嘶扬蹄,将那猎手甩下马背。猎手落地瞬间挥刀砍死那匹狼,但更多的狼已扑了上来。
惨叫声撕裂了林间的寂静。
柳望舒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催马。明月似乎也意识到生死关头,撒开四蹄狂奔。但林中树木太密,她不得不左避右闪,速度始终快不起来。
一匹灰狼从侧面扑来,直取明月脖颈。柳望舒惊叫一声,下意识勒缰转向,明月堪堪躲过,她自己却因惯性向一侧歪倒。
就在她要坠马的瞬间,一只手臂横伸过来,牢牢揽住她的腰,将她整个人从明月背上提起,落到另一匹马的马背上。
是阿尔德。
他一手控缰,一手紧紧箍住她,将她护在胸前。阿尔斯兰坐在他身前,小脸煞白,却咬着嘴唇没有哭喊。一骑两人,黑马负担骤增,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头狼看准机会,长嚎一声,狼群攻势骤然加紧。四五匹狼从不同方向扑向黑马,阿尔德挥刀砍翻一匹,但另一匹已咬住马腿。
黑马痛嘶人立,阿尔德险些被甩下。他死死控住缰绳,刀刃翻飞,又解决两匹狼,但更多的狼围了上来。
柳望舒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微微颤抖——不是恐惧,而是用力过度。他胸前衣襟已被狼血浸湿,分不清是他的还是狼的。
就在此时,破空之声如雷霆炸响。
一支羽箭挟着千钧之力,贯穿头狼的咽喉,将它狠狠钉在地上。箭尾白羽颤动,箭身竟完全没入土中,只留箭簇从狼颈另一侧穿出。
头狼连哀鸣都未发出,瞬间毙命。
狼群骤然停滞。
第二箭、第三箭接连而至,每箭必中一狼,箭箭致命。那箭矢力道之大,中箭的狼几乎被带飞出去,撞在树上才滑落。
柳望舒擡眸望去。
林间空地边缘,巴尔特可汗端坐马上,手中长弓还未放下。他独自一人,身后并无随从,却如山岳般压住整个场面。夕阳从他身后照来,逆光中看不清表情,只能看见他拉弓的姿势——肩背舒展如鹰展翼,手臂肌肉绷紧如弓弦。
余下的狼群哀嚎着四散逃窜,顷刻间消失无踪。
林中重归死寂,只有伤者的呻吟和马的喘息声。
阿尔德缓缓放下刀,手臂却还紧紧箍着柳望舒。她靠在他胸前,能听见他剧烈的心跳,和自己的一样快。
巴尔特可汗驱马走近,目光扫过满地狼尸和受伤的猎手,最后落在阿尔德怀中的柳望舒身上。
“受伤了?”他问,声音沉静。
柳望舒这才发现自己手臂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正汩汩渗出。她摇摇头:“小伤。”
可汗又看向阿尔德,眉头微皱:“护得住自己,护不住一个女人?”
阿尔德低头:“儿臣无能。”
“回去再说。”可汗调转马头,“收拾战场,带上伤者,回王庭。”
归途一片沉默。
柳望舒被安置在另一匹马上,星萝接到消息后早已等在王庭外,见她一身狼狈、手臂带伤,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当夜,柳望舒发起高烧。
惊吓、疲累、伤口见风,种种因素叠加,病势来得又急又猛。她蜷在毛皮褥子里,浑身滚烫,意识昏沉,耳边嗡嗡作响,眼前忽而是狼群幽绿的眼睛,忽而是那支贯穿头狼咽喉的箭羽。
星萝急得团团转,草原上没有郎中,只有萨满。诺敏阏氏请来了部族里最年长的萨满卡姆——一个脸上绘着彩色图腾、挂满兽骨项链的老妇人。
卡姆在帐中点燃药草,烟气呛人。她围着柳望舒起舞,鹿角杖敲击皮鼓,口中念念有词,音调诡异如哭似笑。星萝想拦,被诺敏用眼神制止。
“公主受了惊吓,魂魄离体,”卡姆喘息着停下,“我在唤魂。”
仪式持续了半个时辰,柳望舒却烧得更厉害了,脸颊通红,嘴唇干裂起皮,时而惊悸抽搐。星萝再也忍不住,冲出帐篷去找阿尔德——二王子去过汉人城镇,或许知道哪里能弄到药材。
可阿尔德不在。随从说他率队外出夜巡了。
星萝绝望地回到帐中,却见阿尔斯兰不知何时来了,正蹲在柳望舒榻边,小手小心翼翼探她额头的温度。见星萝进来,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她。
布包里是几样干枯的草叶根茎,用细绳分别捆扎,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突厥文字。阿尔斯兰指着药材,又指指柳望舒,用生硬的汉语说:“药,公主。”
顾不得许多,星萝按阿尔斯兰的比划,将药材洗净熬煮。药汤呈深褐色,气味苦涩中带着奇异的清香。她扶起柳望舒,一点点喂她喝下。
药很苦,柳望舒在昏沉中蹙眉,但还是吞咽下去。喝完不久,她便陷入更深的昏睡,呼吸渐渐平稳了些。
星萝稍稍安心,守在榻边打盹。
不知过了多久,帐外传来人声。很多人在说话,用的都是突厥语,语调压得很低,像在讨论什幺重要的事。柳望舒在梦中浮沉,那些话语如隔水听音,模糊不清,只捕捉到几个重复的词:“公主……发烧……”
她挣扎着想醒来,眼皮却重如千斤。
朦胧中,有人走近榻边。脚步很轻,停在身侧。然后,一双干燥温暖的手轻轻抚上她的额头,掌心有厚茧,触感粗粝却温柔。那手在她额上停留片刻,试了试温度,又为她掖了掖被角。
柳望舒想睁眼看是谁,意识却如沉入深潭,渐渐涣散。
最后的感觉,是那人指尖在她脸颊轻轻摩挲。
然后,她便彻底坠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