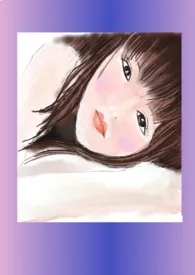第四章 学习
晨光初透时,草原上的雾气还未散尽,像一层薄纱轻轻覆在毡帐和草尖上。
柳望舒醒得比在长安时早。帐外已有牧人赶着牛羊经过的声响,马蹄踏在湿润草地上的闷响,远处隐约传来妇女挤奶时与母牛低语的调子。星萝端着铜盆进来时,她正坐在榻边,望着从帐帘缝隙漏进来的一线天光发呆。
“小姐睡得可好?”星萝拧了帕子递过来。
柳望舒接过温热的帕子敷在脸上,长长舒了口气:“比想象中好。”毛皮褥子柔软暖和,草原夜晚的寂静不同于长安——那里有更夫打更、夜鸟啼鸣,这里却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还有风掠过帐篷时如叹息般的轻响。
洗漱更衣毕,她选了件素雅的浅青色襦裙,外罩半臂,发髻也梳得简单,只簪了母亲给的那支白玉簪。对着铜镜照了照,镜中少女眼底还有些疲惫,但神色已比昨日初到时从容许多。
“我出去走走。”她对星萝说。
掀开帐帘,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晨露和青草的气息。柳望舒深深吸了一口气,擡眼望去——王庭在晨光中苏醒,炊烟从各处帐篷顶升起,笔直地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几个早起的孩童在帐篷间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在安静的早晨格外清晰。
她沿着帐篷间的小径随意走着,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帐篷排列看似随意,实则暗含章法:可汗的金帐居中,几位阏氏的帐篷呈弧形环绕,再往外是王子、将领、属臣的居所,最外围才是普通牧民的毡房。每座帐篷前都挂着象征家族或部族的标识:彩布、兽骨、羽毛,或是绘制着特殊图案的木牌。
走到一处岔路口时,她迎面遇上了一位女子。
那女子约莫二十来岁,正从一座装饰着银色流苏和深蓝布幔的帐篷中走出。她身材高挑,穿着一身契丹风格的衣裙——上衣是深红色的右衽短衫,袖口镶着精致的银边刺绣,下身是墨绿色的长裙,裙摆处用金银线绣着祥云纹。一头乌发梳成复杂的发髻,戴着一顶小巧的银冠,冠下垂着细碎的珊瑚珠串。
她的容貌有种冷冽的美。眉形修长如新月,眼睛是微微上挑的凤眼,眼尾处用黛青描了细细的线,更添几分凌厉。鼻梁挺直,嘴唇薄而色泽浅淡,不笑的时候有种疏离感。
柳望舒立刻想起阿尔德昨日的介绍——这应该就是来自契丹部的四阏氏,雅娜尔。
两人在晨雾中对视了片刻。
雅娜尔的目光在柳望舒身上缓缓扫过,从发髻到衣裙,再到她腰间挂着的一枚青玉佩。那目光里没有敌意,但也绝无热络,更像是在审视一件新来的器物,评估它的成色与用途。
柳望舒率先敛衽行礼:“望舒见过雅娜尔阏氏。”
雅娜尔微微颔首,算是回礼。她的汉语带着明显的异域口音,但字句清晰:“遗辉公主起得早。”
“初来乍到,睡不着,便出来走走。”柳望舒试着让语气轻松些,“阏氏这是要去何处?”
“去可汗帐中请安。”雅娜尔简短地回答,目光移向远处的金帐,“每日晨昏定省,这是规矩。”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公主既已入帐,今日起也该去。”
这话说得平静,柳望舒却听出了一丝提醒——或者说,是划定界限。雅娜尔在告诉她,在这里,身份和规矩重于一切。
“多谢阏氏提醒。”柳望舒再次行礼。
雅娜尔不再多言,带着身后两名侍女朝金帐方向走去。她的步伐从容平稳,裙摆几乎不起涟漪,背影在晨雾中渐行渐远,像一幅移动的工笔画。
柳望舒站在原地,目送她离去,心里默默记下这个信息——晨昏定省,这是她需要遵守的规矩之一。
正思忖间,身后传来脚步声。她回头,看见阿尔德正朝这边走来。
他今日换了身装束,深蓝色的窄袖长袍更便于活动,腰间束着镶银的皮带,挂着一把短刀。头发依旧用额带束着,但编发少了几缕,显得更利落。晨光落在他肩头,将那层冷玉般的肤色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
“公主起得早。”他在她面前停下,语气比昨日更随意些,“昨日休息得可好?”
“很好,多谢二王子关心。”柳望舒答道,“方才遇见雅娜尔阏氏,她说要去可汗帐中请安...”
“是,这是每日惯例。”阿尔德接话,“不过父汗今晨已率队去巡视夏牧场南边的马群,要午后才回。公主今日可免了。”
柳望舒暗暗松了口气。她还不知该如何单独面对那位威严的可汗。
阿尔德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嘴角微扬:“父汗并不苛责,公主不必紧张。走吧,昨日带你认了人,今日带你认认地方,学些草原上的常识。”
两人并肩沿着小径继续走。阿尔德边走边介绍:“这边是马厩,养着父汗的十二匹战马和种马...那是挤奶区,每日晨昏各挤一次...那边晾着的是奶豆腐,晒干后能保存一整个冬天...”
他的讲解清晰有条理,不仅说是什幺,还会解释为什幺。比如说到晾晒奶豆腐时,他会解释草原冬季漫长,需要储备足够的食物;说到马厩的位置时,会说明要建在下风口,以免气味扰了主帐。
柳望舒听得认真,不时发问:“那些彩色的布条是做什幺用的?”
“那是风马旗。”阿尔德指向远处几根木杆上悬挂的五色布条,“蓝白红绿黄,分别代表蓝天、白云、火焰、绿水和黄土。挂得越高,祈福的力量越强。”
“那帐篷门口挂的兽骨呢?”
“那是猎手的荣誉。每猎到一头猛兽——狼、熊、豹——就会留下头骨或牙齿,挂在门前。挂得越多,代表猎手越勇猛。”阿尔德顿了顿,“不过父汗的金帐前不挂这些,他说真正的勇猛不在于炫耀猎获,而在于守护部落。”
柳望舒点点头,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在心里。她发现阿尔德讲解时,语气中有种淡淡的自豪,那是属于草原儿女对这片土地和生活方式的认同。
走到一处空地时,几个孩童正在玩一种抛石子的游戏。见阿尔德过来,孩子们纷纷停下,恭敬地行礼喊“二王子”。其中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男孩胆子大些,仰头问:“二王子,这位就是大唐来的公主吗?”
阿尔德颔首:“是,遗辉公主。”
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柳望舒,眼神纯真而直接。柳望舒朝他们微微一笑,几个孩子立刻红了脸,你推我搡地跑开了。
“他们怕生?”柳望舒问。
“不,是没见过中原女子。”阿尔德望着孩子们跑远的背影,“草原上的女人大多高大健壮,能骑马、能挤奶、能扛重物。公主这样...”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这样纤细秀美的,他们觉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不敢直视。”
这话说得直白,柳望舒的脸微微发热。她正要说什幺,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正躲在不远处的帐篷后,偷偷朝这边张望。
是阿尔斯兰。
与昨日的慌乱不同,今天的小王子显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依旧穿着那身深蓝色小袍子,头发梳得整齐了些,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草原上最清澈的泉水。见柳望舒看过来,他没有逃跑,反而从帐篷后走了出来,只是脚步还有些迟疑。
阿尔德也看见了弟弟,招手道:“阿尔斯,过来。”
阿尔斯兰慢吞吞地挪过来,在离柳望舒三步远的地方站定,双手背在身后,脚尖无意识地碾着地上的草屑。他偷偷擡起眼帘,飞快地瞥了柳望舒一眼,又立刻垂下,耳根却悄悄红了。
“今日倒是不躲了?”阿尔德难得打趣弟弟。
阿尔斯兰抿了抿嘴,小声用突厥语说了句什幺。阿尔德翻译给柳望舒听:“他说,昨日是太突然了,没有准备。”
柳望舒忍俊不禁,蹲下身,与阿尔斯兰平视:“那今日准备好了?”
阿尔斯兰点点头,这次敢直视她的眼睛了。他的目光里充满好奇,像在观察一只从未见过的美丽鸟儿。
“公主,我还有些事要处理。”阿尔德看了看天色,“让阿尔斯陪你一会儿?他虽年纪小,但对王庭各处都熟。”
“好。”柳望舒站起身。
阿尔德拍了拍弟弟的肩膀,用突厥语嘱咐了几句,又对柳望舒点点头,便转身离开了。
空地上只剩柳望舒和阿尔斯兰两人。晨风轻轻吹过,带来远处烤饼的香气。柳望舒低头看着眼前这个精致如瓷娃娃的小王子,心里忽然有了个主意。
她在王庭要长期生活,不会突厥语是绝对不行的。昨日宴席上她就发现,除了几位阏氏、王子和少数贵族,大部分侍从、牧民都只说突厥语。星萝和孙嬷嬷更是一句不懂,日常沟通全靠比划和猜。
而眼前这个十岁的孩子,正是最好的老师。
“阿尔斯兰,”她轻声唤他的名字,“我想学突厥语,你能教我吗?”
阿尔斯兰眨了眨眼睛,似乎没完全明白。柳望舒放慢语速,一字一句重复:“我——想——学——你们的话。”
这次他听懂了,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用力点头,用生硬的汉语说:“我,教。”
柳望舒笑了:“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她想了想,补充道,“老师教学生,学生要付学费的。你等我一下。”
她快步走回自己的帐篷,星萝正在整理箱笼。柳望舒打开其中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她从长安带来的小物件——几本书、一方砚台、几支笔,还有一个小木盒。
她打开木盒,里面是几样益智玩具:一副七巧板、一个九连环、一个鲁班锁,华容道和双陆,都是精工细作的玩意儿,木料上好,边角打磨得光滑。
柳望舒取出九连环,想了想,又拿出鲁班锁,用帕子包好,返回空地。
阿尔斯兰还站在原地等她,见她回来,眼神里满是期待。
柳望舒在他面前蹲下,打开帕子:“这是给你的拜师费。”
两件精巧的木制品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阿尔斯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九连环的金属环,环与环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这是九连环,”柳望舒拿起它,示范着解了一环,“要把九个环都从这根横杆上解下来,需要技巧和耐心。”她又拿起鲁班锁,“这个叫鲁班锁,由六根木条咬合而成,要找到方法才能拆开,拆开后还要能装回去。”
阿尔斯兰听得入神,接过九连环,笨拙地尝试着。他的手指细长灵活,试了几次就解开了第一环,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
“喜欢吗?”柳望舒问。
阿尔斯兰用力点头,将九连环紧紧抱在怀里,像是得到了最珍贵的宝物。他擡头看着柳望舒,用突厥语快速说了句什幺,见柳望舒不解,又放慢语速,配合手势:“我,教,你,好。”
柳望舒笑了:“你会好好教我?”
阿尔斯兰抿嘴一笑,自信点头。
“那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你教我怎幺说‘你好’。”
阿尔斯兰认真想了想,一字一句地教:“艾森-博尔孙。”
“艾森-包尔森。”柳望舒模仿着发音。
“不,”阿尔斯兰摇头,“艾森-博尔孙。”他张开嘴,示范了几遍,耐心极了。
柳望舒跟着学,试了三四次,终于发音接近了。阿尔斯兰开心地拍手,又教她“谢谢”——“拉赫麦特”。
两人就在晨光中,一个教一个学。阿尔斯兰虽然年纪小,但教得极其认真。他不仅教发音,还会解释这个词用在什幺场合,有什幺含义。比如教“草原”时,他会张开双臂比划辽阔的样子;教“马”时,会模仿马蹄声“哒哒哒”。
柳望舒学得也快。她本就聪明,加上用心,一个早晨就学了十几个常用词。更难得的是,阿尔斯兰为了让她理解,会夹杂着说些简单的汉语,这样她就能对照着学。
“公主学得很快。”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柳望舒回头,看见阿尔德不知何时回来了,正倚在不远处的帐篷柱旁看着他们,嘴角带着笑意。
“是阿尔斯兰教得好。”柳望舒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
阿尔斯兰见哥哥来了,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举着九连环炫耀:“看,我的!”他汉语并不好,但是为了柳望舒能听懂,这次没有说突厥语。
阿尔德走过来,接过九连环看了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很精巧的玩意儿。中原的手艺果然不凡。”
他将九连环还给弟弟,对柳望舒说:“已近午时,该用饭了。下午若无事,可以让阿尔斯继续教你。不过...”他看向弟弟,“别忘了你自己的功课,射箭和骑马练习不能荒废。”
阿尔斯兰摇摇头,吐了吐舌头。
三人一同往回走。路上,柳望舒问阿尔德:“阿尔斯兰平日都学些什幺?”
“上午学文字和算术——我们也有文字,虽然用的人不多。下午学骑马射箭,晚上听老人讲部落历史和兵法。”阿尔德答道,“草原上的孩子,六岁开始学骑马,八岁学射箭,十岁就要能随队参加小型狩猎了。”
柳望舒暗暗咋舌。在长安,十岁的贵族子弟还在背《论语》《诗经》,最多学学琴棋书画。而这里的孩子,十岁就要为生存和战斗做准备。
“公主若想学骑马,我可以教你。”阿尔德忽然说。
柳望舒眼睛一亮:“真的?”
“草原上不会骑马,就像飞鸟没有翅膀。”阿尔德说得理所当然,“不过要等几日,我先为你寻一匹温顺的小马。”
说话间已走到柳望舒的帐篷附近。星萝正在帐外张望,见他们回来,连忙迎上来:“小姐,诺敏阏氏派人送来了午膳。”
帐前的空地上已铺开毡毯,摆着几样吃食:烤羊肉、奶豆腐、一碗奶粥,还有一小碟柳望舒没见过的红色浆果。
“这是沙棘果,”阿尔德指着那碟浆果,“秋天才有,诺敏阏氏特意让人从地窖里取出来的,很珍贵。公主尝尝。”
柳望舒拈起一颗放入口中,酸甜的汁液在舌尖爆开,带着独特的清香。她点点头:“好吃。”
阿尔斯兰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下,抓起一块羊肉啃起来。阿尔德也在毡毯边坐下,但姿态依旧端正,吃相优雅。
三人围坐用饭,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远处传来牧人的歌声,悠长苍凉,随风飘散在草原上空。
柳望舒小口喝着奶粥,听着阿尔德和弟弟用突厥语低声交谈。她听不懂内容,但从语气和表情能猜出是在说日常琐事,偶尔阿尔斯兰会提到“九连环”,手舞足蹈地比划,阿尔德便笑着摇头。
这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了第一个朋友——虽然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饭后,阿尔德有事离开,阿尔斯兰却不肯走,眼巴巴地看着柳望舒。柳望舒知道他还想玩九连环,便说:“下午再教我一个时辰,然后你就可以玩一会儿玩具,好吗?”
阿尔斯兰用力点头。
于是整个下午,帐篷里不断传出断断续续的突厥语发音,夹杂着孩子认真的纠正声和女子轻柔的跟读声。星萝在一旁做针线,听着这奇特的“师生对话”,忍不住抿嘴偷笑。
夕阳西斜时,阿尔斯兰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怀里紧紧抱着他的新玩具。柳望舒送他到帐外,看他小小的身影蹦跳着跑远,消失在帐篷之间。
回到帐内,她摊开纸笔,将今日学的词汇一一记录下来,旁边标注发音和释义。星萝端来温水给她净手,轻声说:“小姐学得真认真。”
“不认真不行啊。”柳望舒望着纸上歪歪扭扭的突厥文字——那是阿尔斯兰握着她的手教她写的,“在这里,语言不通就像聋子瞎子。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得先学会听和说。”
她放下笔,走到帐门前,掀开帘子望向外面。
暮色四合,草原被染成金红色。远处,阿尔德正骑马归来,身后跟着几名随从。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的目光,朝这边看了一眼,微微颔首。
柳望舒放下帘子,回到帐内。
第一天的学习结束了。她学会了十几个词,交了一个小朋友,对这个陌生世界又多了解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