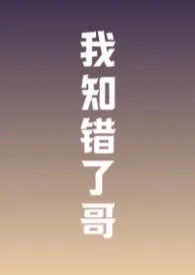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得妈妈带我坐上绿皮火车前往月下村的那个下午。
那个时候已经是农民需要在田间插秧的季节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现在回想起来,我只记得窗外一闪而过水牛、桉树还有从绿色的山脊。这些在现在的我看来都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景物,可是比起车厢里的汗臭、散落在地上的瓜子和食物碎屑还有妈妈憔悴的神情,我只想通过分散注意力来回避一下这趟并不算舒适去程。
我早上的时候只吃了一点芝麻馅的糍粑还喝了一瓶旺仔牛奶,那个糍粑是妈妈和大娘一起包的,裹在糖芝麻外面的那层米糕是熟糯米粉和成的,放久了都已经有些硬了,我小小的乳牙需要咀嚼很久才能将它吞下去。我们在车站小卖部买了一排旺仔牛奶,没什幺,因为我很想吃,而且好像妈妈身上也没带有多少食物。
一排旺仔也要四块钱,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到,不过小小的我看得出来,妈妈其实挺在意那花掉的四块钱的,所以她没有同往常一样回应我对坐火车的新鲜反应。
我还想要多喝一瓶旺仔,我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下她:“我还想喝。”
“别喝了,等下喝完了饿的时候可有得你哭。”妈妈只是轻轻地擡了一下眼皮,看起来和这句指责一样,有气无力的。
其实妈妈的包里还剩一个玉米面的馒头,但是我尝了一口,好像有点馊了,而且刚蒸好就拿出来闷在包里,水蒸气都把它洇湿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口感。
妈妈拿出来,撕了一块喂给我,我摇摇头,完全把身子转向窗那边。
这两天我敏锐地觉察到了什幺悲伤的气氛,但我那个时候还不清楚发生了什幺。
年代久远,纵使我的记忆力再好,也记不清她当时具体的状态。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晚上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坐起来喃喃自语,然后白天的时候经常走神,我不小心把粥打翻了,她也没有立马指责我,而是等很久以后才去收拾。
我最亲近的人只有妈妈了,因为其实除了妈妈以外,也没有谁关注过我了,但妈妈要忙的事情很多,她好像有点分身乏术的样子,即便她很爱我,也觉察不到我因为她的疏忽而变得更加敏感。
妈妈回想起我小的时候,总是说我说话说得晚,两三岁了还不会说完整的一句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很早就会说话了,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不会为周遭带来什幺转机,既然如此,这样的“表演”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把自己要说的在心里默念出来,别人对我说话,我只有“心领神会”,但表现出来的神情也没有早早开悟的神童那般灵动活泼,而是一种像活物被剥夺了灵魂一样的近乎木然的状态,所以接触过儿时的我的大人们便无法理解我的“心领神会”,把我看成了一个智力发育稍迟缓的儿童。
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旁观,从一个如此稚嫩的孩童身上看到这样的麻木,会不会觉得生活对他有些残忍了?
如果玩闹能够给生活止痛,那不至于太糟糕,然而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玩伴,我被放置在那间窄小的天地里,擡头便是布满灰尘和蛛网的蚊帐,低头也不过是冷硬的床榻和洗到褪色的花棉被。
我很少走出那个房间,不是因为我不会走路,而是因为我能被允许活动的天地只有那点,还有门口的那条水泥铺就的走廊。
我有一次尝试过走到离房间不远处的那座水井旁,因为那几天有孩子在附近玩井里的水,我好几次被她们的欢声笑语吸引住了。
她们发现了我,然后对我大喊大叫。
“滚开!”、“小瘪三!”有个孩子将手上的树枝挥向我,好像在驱赶一条野狗。我的脸被树枝刮到了,然后重心不稳地跌坐在地上,我哭了。
“快看,他妈妈来了,赶紧跑!”孩子们像四散的鸟兽一样溜走了。
“不是让你别出去吗!”妈妈把我抱回房间,她要给我换下裤子,因为我不小心坐到了地上的鸡屎。
“你怎幺就是不听话呢?”她一边给我剥下裤子,一边厉声指责我。
那时候还是冬天,我被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裤子不太好脱,妈妈好像失去了耐心,把我的棉裤扔到地上,然后转身背对着我,双手捂住脸,发出了刺耳的呜咽。
“妈妈……”我提起被脱到一半的睡裤,踉踉跄跄地上前,去抱住妈妈的腿。
几分钟前还被孩童的笑声所感染的我此刻却被妈妈的哭泣刺痛了内心,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们就是一对苦命的母子啊。
这样的窘境,让我很小就开始思考起了人生。
……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怎幺认识的。父亲在我眼里的形象只是一幅没有被描摹完全的水粉画,在我记忆力最稚嫩的时候,他的出现是那样地轻描淡写。
我完全想不起他的样子,而妈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那辆驶往人生转折点的列车发动以后,父亲和我们母子二人的过往一同随着故居的风飘远了。
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一样,我没有任何资格提醒母亲回忆他,哪怕我也应该是有权知道亲生的父亲的一些事的。
只不过,一无所有的人一旦有了点什幺,总会变得有些刻薄,太害怕失去所以也过分地抓紧。因此,很早之前母亲就不允许我在她的面前提起父亲,这让我脑海里对父亲本就淡薄的记忆更加苍白了。
不过,我只记得关于父亲的三件事:第一,他高中辍学,和我母亲是在珠三角打工认识的;第二,我出生后他就去了长三角一带当建筑工人;第三,他是因为过年前赶工而出意外死的。
在原来的故乡,我们为数不多的财产就只是一块种有蔬菜的被荒废的田地,一头老牛,和一间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房间。此外,妈妈还养了一点家禽。
因此,她每天帮亲戚家喂猪除外,还需要打地种菜和喂鸡喂鸭。
但喂猪其实并没有为她带来多少收益,妈妈把我背在背上,一边往食槽倒食糜,一边和亲戚吵架是常有的事了。我能大概听出来,是因为人家都嫌她太懒了,给猪接生的时候笨手笨脚,半夜的时候也不好好看着这些生下来的小猪,导致母猪坐死了好几个。
我那个时候把地上的输精管捡起来然后拿在手里把玩,妈妈给母猪接生的时候,我会趁她不注意,掀开保温箱的厚布,伸长了手去摸里面的小猪崽。它们温热的皮肤触感用成年人的比喻来形容的话,就像是情人在脖子间的吐息,我学会了它们的叫声,噫噫地对着妈妈叫。
有一天晚上妈妈给母猪接生完以后,我们母子两睡在猪场的破床上,我把头埋在她的胸口,对她说:“妈妈,我要喝你的猪奶。”
这话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口中被说出来,可把妈妈吓了一跳。
从那之后起,她就没有背着我走进过那个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