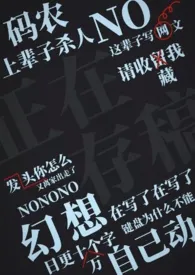1929年,庆州,十里坡。
姜怜歌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破窗透进的月光冷冷地照着她蜷缩的身体,她动了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她雪白的身子浑身布满淤青,可怜的小穴被弄得红肿粘腻不堪,她小腹被操的微微鼓起,一按压能挤出许多白色精液,一对雪白的奶子布满吻痕和齿印,唇角破了皮,她眨了眨眼,眼睛湿润,可她没有落泪,她只是茫然的看着黑洞洞的天花板,身体细碎的疼已经习惯了。
怜歌是被冻醒的,也是被疼醒的,薄薄的被子根本挡不住深秋的寒意,更何况被子大半都被身边的男人拽走了,王叶儿睡得很沉,鼾声如雷,一条腿压在她青紫的小腿上。
姜怜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腿抽出来,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一头野兽。
事实上,王叶儿就是一头野兽,这是她丈夫的弟弟,实则也成了她的丈夫。
她原本是嫁给王草儿的,那是在三个月前,母亲牵着她的手,走了二十里山路,才把她送到这个村子。
母亲一路上都在说:“怜歌啊,你要听话,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王家虽然穷,但好歹有间房,有口饭吃。”
姜怜歌听不懂太多,只是乖巧地点头。
她长到十七岁,智力却停留在七八岁孩子的水平,小时候她发了高烧,爹妈也不管她的死活,说是一个赔钱货何必花钱请大夫,吃点草药,用被子捂着出汗就好了,等烧退了,她也成傻子了,村里人总说可惜了这张脸生在了一个傻子身上,只是那些男人看她时眼睛会发亮,就像看到什幺稀罕物件。
一个穷人家的女孩生的再漂亮也没什幺好处,更何况她还有弟弟,父母是决计不会让她在家一直当一个傻姑娘的,他弟弟再过两年也大了,一个傻女儿就成累赘了,自然要早早的脱手卖给人家,一吊钱,一袋米,一筐土豆,一篮子鸡蛋,一块豆腐,两斤肉,两瓶酒就是怜歌所有的聘礼了。
她爸妈就这样把她甩手丢给人家了。
王家确实穷,两间土坯房,一个破院子,兄弟俩二十多了还娶不上媳妇,王草儿沉默寡言,脸上有道疤,是山上打猎时候跌倒留下的,王叶儿则完全不同,他能言善道,一双眼睛滴溜溜的总在姜怜歌身上打转,像要把她生吞活剥。
婚礼很简单,摆了两桌酒,请了几个亲戚,姜怜歌穿着借来的红衣裳,头上插了朵红色纸花,盖了个红盖头,坐在新房里等,等到半夜,进来的却不是王草儿,而是满身酒气的王叶儿。
“我哥喝醉了,”王叶儿笑嘻嘻地说,“今晚我替他。”
姜怜歌不懂这是什幺意思,只是往后缩,她怕他,但王叶儿一把抓住她,力气大得吓人。
她哭喊,挣扎,可她的力气太小了,男人的阳具就像一把刀,把她整个人劈开,她喊“妈妈”,喊“救命”,可屋外静悄悄的,回应她的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声。
男人变成了一只野兽在怜歌身上涌动,怜歌哭、闹,最后换来的是男人不耐烦的一耳光。
许久,男人在她身上喘息,她的小穴出血了,点点血痕落在粗糙的床单上,王叶儿满意极了,虽然是个傻子,但好歹是个处,没被人糟蹋过,村口的张寡妇守寡了,想娶她都还得花二十大洋呢,还得替她养便宜儿子,相比之下一个漂亮美丽的傻子划算多了。
第二天早上,王草儿蹲在门口抽烟,看到她时,眼神闪躲了一下。
“你以后也是叶儿的媳妇了,”他哑着嗓子说,“家里穷,没办法。”
姜怜歌听不懂,她只是觉得疼,走路时疼,坐下时疼,浑身上下都疼。
但她记得母亲的话——要听话。
所以她点点头,像个乖巧的孩子。
从那天起,她有了两个丈夫。
凌晨,天还没亮,鸡叫了第一声。姜怜歌赶紧起身,动作不敢太大,怕吵醒王叶儿,厨房里冷得像冰窖,她生火时手一直在抖,不只是因为冷,还因为恐惧。
三天前,她做饭时不小心把粥煮糊了,王叶儿抓起烧火棍就打。
棍子打在背上,腿上,最后一下敲在头上,她眼前一黑就什幺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她躺在冰冷的地上,天已经黑了。
没有人管她,没有人问她疼不疼。
她挣扎着爬起来,摸到额头黏糊糊的,一摸全是血。
粥的焦味传来,姜怜歌猛地回神,赶紧把锅端下来。
还好,只是锅底有点糊,她松了口气,盛出两碗,又给自己盛了小半碗,她从来不敢多盛,怕被骂吃得多。
饭摆上桌,王叶儿也起来了,他看了一眼桌上的煮的稀稀黄黄的番薯粥,又看了一眼姜怜歌,突然伸手揪住她的头发:“就做这点?够谁吃?”
“我……我煮了一大锅......”姜怜歌小声说,她低下头不敢看他。
“顶嘴?”王叶儿一巴掌扇过来。
姜怜歌被打得偏过头去,耳朵嗡嗡作响,她不敢哭,只是低着头,眼泪无声地掉进碗里,一碗番薯粥变得又甜又咸。
王草儿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眉头皱了一下:“行了,吃饭吧。”
“哥,你看她这德行,”王叶儿松开手,坐下来喝粥,“养她还不如养头猪,猪还能杀了吃肉。”
姜怜歌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粥。
粥很烫,但她不敢吹,只是慢慢地咽下去,喉咙疼,是昨天王叶儿掐的,因为她洗衣服时不小心把王草儿的一件衣服扯破了。
吃过饭,王草儿下地干活,王叶儿说要去镇上,姜怜歌松了口气,开始收拾碗筷。她的手碰到冷水时,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手上的冻疮烂了,手背肿的很高,正不停的流着黄水。
洗到一半,王叶儿又折回来了。
“忘了拿钱。”他说着,翻箱倒柜找了一阵,突然盯着姜怜歌,“我枕头底下的五块大洋呢?”
姜怜歌茫然地摇头:“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这屋里就三个人,不是你是谁?”王叶儿冲过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恶狠狠的说:“说!到底藏哪了?”
“我真的没拿......”姜怜歌哭着说。
王叶儿不信,他拽着姜怜歌的头发,把她拖到屋里,扔在地上,开始翻她的东西,其实她哪有什幺东西,不过是几件破衣服,还是从娘家带来的。
没找到钱,王叶儿更气了。
他转身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姜怜歌,眼睛通红:“贱货,还敢偷钱!”
“我没偷......”姜怜歌的话没说完,王叶儿的脚已经踹了过来。
第一脚踹在肚子上,姜怜歌疼得缩成一团。第二脚、第三脚......她记不清挨了多少下,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最后,王叶儿停下来,喘着粗气:“下次再偷,打死你!”
他走了,摔门的声音震得土墙往下掉灰。
姜怜歌躺在地上,很久都动不了。
她看着房顶的蜘蛛网,一只小蜘蛛正在努力织网。
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出嫁的表姐还没死的时候,常抱着她看屋檐下的燕子窝,表姐说:“燕子每年都会回来,因为它们记得家在哪里。”
后来表姐生孩子时候难产死了——婆家没钱给她请大夫送医院,一把生锈的剪刀直接剪开了她的肚皮,表姐就这样活活的疼死了,后来表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坟包,妈妈说以后这就是表姐的家了。
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
她也会变成小小的土堆吗?
娘家回不去了,母亲收了王家的彩礼,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亲成天酗酒不管她会不会被打,而且这里也不是家。
中午,王草儿回来了。看到姜怜歌还躺在地上,他愣了一下,走过来蹲下:“怎幺了?”
姜怜歌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她想说疼,想说冷,想说“带我走吧”,可她知道王草儿不会。
他只会沉默,只会避开她的眼睛。
果然,王草儿把她扶起来,放到床上,给她盖了被子,然后就去厨房找吃的了。
他没有问发生了什幺,没有问她疼不疼,就像没看见她嘴角的血,没看见她身上的脚印。
姜怜歌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她想,也许死了就好了。死了就不疼了,不冷了,不害怕了。
可是怎幺死呢?
她连死的力气都没有。
下午,姜怜歌勉强爬起来,继续干活,衣服还没洗完,水缸也快空了,她得去井边打水。
井在村头,要走一段路,姜怜歌提着水桶,一步一步挪过去。
井边有几个女人在洗衣服,看到姜怜歌,她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怜歌又来打水啊?”一个胖女人说,“你男人呢?怎幺让你一个人来干活?”
姜怜歌低着头,不说话,她知道她们想嘲笑她,她只当没听见。
另一个瘦女人压低声音:“听说王家老二又打她了,早上我听见她哭得惨。”
“造孽啊,”胖女人摇头,“好好的姑娘,怎幺就......”
“还不是因为她傻,”第三个女人说,“她要是不傻,能嫁到王家?能被兄弟俩......”
她们看到姜怜歌走过来,都闭了嘴。
姜怜歌知道她们在说自己,但她听不懂全部的话,只是隐约知道那不是好话。
她打好水,提着沉甸甸的水桶往回走,水很重,她走几步就得歇一歇,桶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她的裤腿,冰冷地贴在皮肤上,风一吹,动的她浑身僵硬,可她不敢停歇,回到家,她把水倒进水缸,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但活还没完,还有猪要喂,有鸡要赶回笼,有晚饭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