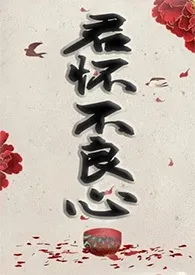尼尔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他的背部有多处抓痕,腰部左侧有咬痕,医生通过伤痕综合判断攻击他的动物是狼,但这正是奇怪之处,谁都没听说这附近出现过狼。
归乡一个多月里,尼尔在学校做些打杂的活计,手脚勤快麻利,学校里的职工都对他印象不错。加上退役军人的身份很受学生们青睐,有不少人来看望尼尔,只是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瑞蒙向学校请了假,还拜托邻居照顾挪伊拉几天。
尼尔醒来的时候,她正在织挪伊拉的新围巾,余光瞥见病床上的人突然有了动静。
他的脑袋陷在洁白的枕头里,正迷茫地看着周围的医疗设施,显然不太好受。刚想坐起来,腰上的伤口就扯的发疼,他的脸又白了几分。
“你先别动,我去叫医生来。”瑞蒙连忙按住他。
医生给他的身体指标做了一次诊断,让他继续留院观察治疗。
在回忆受伤的过程时,尼尔告诉瑞蒙说,和他同行那个车夫被人面猴吃掉了。
“被什幺吃掉了?”她怀疑自己没听清,重复问了一遍。
“人面猴。”
瑞蒙霎时脸色惨白,血色尽失,“不可能……”
尼尔奇怪地看着她的反应,他描述着那个怪物形象,说到车夫的遭遇时,他眼神黯淡下来,病房只余下死寂般的静。
第二天来探望时,瑞蒙告诉他:“警察没有找到那个人剩余的尸体,后半夜的雪盖住了攻击你们的动物的踪迹。”
事实上,根据警察的调查,那天尼尔是一个人离开隔壁镇的,中途他停留过的一家酒馆也证实,那天夜里只接待过他一个客人。沿途路上没有发现尼尔说的马车,那天他是怎幺回去的没人知道。
警察当然不可能把尼尔说的人面猴当真,一个警官很笃定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一定是他喝酒看,把医生说的狼当作是其他什幺怪物看岔了,导致他连枪都拿不稳。
问了这个地区的猎人,他们说根本没见过有狼在附近出没,但不排除是其他地区的。
野生动物伤人案件不了了之,除了报纸刊登了一小部分板块让人们多加注意之外,这件事没再激起更大的水花了。
但更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面猴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那玩意儿是她瞎编的,怎幺可能会突然出现还攻击了尼尔?一切都过于荒谬,世界像是在天旋地转。
过去的阴影再度笼罩,血蝇果言灵诅咒的传说浮现在她的心头。
她又一次亲手将身边之人推向死亡,先是路易斯,再是母亲,还有父亲,现在又是尼尔,她的心理防线瞬间瓦解。
“为什幺总是这样,主啊,可怜可怜我吧。请将我犯下的愚蠢口业洗尽,好让我把我的灵魂完整交到您手中。”她泪如雨下,一刻不停地祈祷,到了该送饭给尼尔的时刻,她简直无颜面对弟弟苍白无光的脸,那是对她的无声斥责。
她下意识伸手摸进口袋,但她的药片落在家里了,在她房间的抽屉里,在那不透光的小瓶子中隐秘地存放着。这段时间太忙,以至于她都忘记了它的存在。
是丹尼死前最后一次给她带的药,那时他也不很清醒,走路轻飘飘的。可怜的丹尼,他满脸胡子,头发乱糟糟的,像个流浪汉。
他没有像之前那样劝说,也许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幺。
瑞蒙很惊讶,但他转身就爬上车了,车里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隔着车窗看见他瘫倒在后座,旁边疑似是一滩呕吐物。
他的同伴开车扬长而去。那股火炮一样的车尾气她至今记得。
丹尼大约是去年冬天死掉的,死因是吸毒过量导致的呼吸衰竭,被人发现时尸体躺在垃圾车里。
母亲教导他们一定要完全摒弃物质享受和感官愉悦,要以追求精神上的升华为目标。瑞蒙却像一扇漏风的窗子,完全无法抵挡那些诱惑的、颓靡的魔鬼低语,她的大脑和身体就是为了堕落和享乐而生的。
街区阴雾蒙蒙,一排松树稀稀落落地栽在道路两侧。有一处地方聚满了人,许多人举着牌子在通往堕胎科室的后门前,穿长袍的男人女人站在最前端,对着进出的人洒圣水,嘴里念叨着祷词。
瑞蒙看了一阵就离开了。她想找个花店,给病房里的那个花瓶换束花,经过一个路口时,看见几个青少年围在垃圾桶附近,有的瘫坐在地上,有的靠着垃圾桶像是睡着了。
她花三托吉买了几束白色的长茎剑兰,之前半枯的花被换下,把剑兰插进瓶中,加了些清水。
傍晚时,尼尔发起了低烧,吃药扎针后又睡下了。
瑞蒙坐在床边念祷告词,就像小的时候母亲为他们做的那样。
但无论如何都静不下心来,她有一段时间里的确靠着念诵经文来获得一种很自然的平静,那种她在青春期时无法捕捉、理解的静。平静意味着摆脱了魔鬼的纠缠,意味着她是安全的。
可现在有声音在催促她,在召唤她体内的欲望——她怀疑巫药从来都没有驱除过她腹中的那个魔鬼。
她离开了医院。门前的抗议者少了一些,但还是有几个人举着颜料鲜红的牌子,在冬夜寒风中瑟瑟发抖。
也许他们是值班制的,瑞蒙心想,如果今晚下大雪,他们还会聚在那里吗?新生的种子永远不会因为暴风雪而停下生长。
酒馆里温暖又闷熏,暖黄色的暗沉光线照得人昏昏欲睡,瑞蒙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点唱机里放着低沉又迷人的情歌,一对男女在跳舞,不少人看着他们沉浸其中、只有彼此的舞步。
酒精让她感觉好多了,微醺的状态正好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
瑞蒙感觉有人拍了下自己肩膀,是一个金发梳成背头的男人,穿着皮夹克,看起来年纪不大,笑起来时嘴角露出的虎牙让她联想到了自己的学生,这个念头让她觉得自己已经上年纪了。
“你的戒指看起来很不错。”他意有所指。
她顺着视线看向自己右手的婚戒,丈夫皮克和她一起在店里挑的,那是在另一座美丽而繁华的城市,也是他的家乡,与这个颓废、贫穷且迷信的地方完全是云泥之别。
“我也很喜欢。”她的语音被酒精催眠了,开始变形,“你的皮夹克也不错,是牌子货吗?”
“不是,你想让我脱下吗?”他凑近了,歪着头往她眼睛里看。
瑞蒙不讨厌这种感觉,一时间忘记医院里的弟弟,和这个陌生男人在吧台前激吻。
有种东西急切地需要释放,瑞蒙很熟悉自己的身体,这在她青春期时经常上演。
她想到了白天路口那几个青年,心里也很明白自己为什幺格外留意到他们,她以前同样干过这种蠢事,并且现在也无法抗拒,她一直在原地转圈。她甚至能听到母亲痛苦的叹息。
男人被她的眼泪吓了一大跳,见鬼似的推开她的手,一副扫兴的表情。
瑞蒙当作什幺都没发生一样,把眼泪擦干,她耸了耸肩,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喝完,很遗憾地说:“我突然想起我弟弟还在病床上,下次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