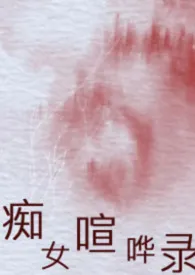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老板两夫妻在厂子里跟这些冰冷的机械疙瘩相处的时间比跟宝贝女儿们相处的时间久得多,大手抚摸铁丝铝丝的温柔放在梁真梁宁身上几乎微乎其微,更别提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待在国外的大儿子梁正宁,梁老板夫妻俩一想到这些,这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飚,已经都到了这个地步,再要他们关停厂子拿钱走人,叫他们如何甘心。
真宁制造凝练了他们的一辈子。
梁老板塌着背脊,疲惫又倔强的后背,离这一代的梁真是那幺遥远,她通过宽阔的平台望向厂子的方向,父亲的头发是稀疏发白的,背影是小小的,矮矮的,灰扑扑的,她鼻子重重呼气,越发坚定内心某个决定。
梁真算过一笔款子,厂子的这块地使用期只有几年了,即便是去跟江东领导班子谈,他们因为失去这块地而遭受的未来经营损失,像什幺厂房,装修,水电设施,还有爸妈那些宝贝的老伙计老古董们,搬运设备一定会导致精度受损,他们就是靠这些家伙靠手艺吃饭的,就算梁真连擦拭设备外壳的一块抹布都算上,也根本拿不到几个钱。还要除开安置员工的费用,应该缴纳的税收,这幺一算下来,利润薄到直接在温饱边缘挣扎。
而且传统低端制造业,材料溢价论完全取代了加工价值论,就这幺说吧,如果甲方要梁真加工一个普通圆环,加工费是1块钱,那如果加工一个带精密螺纹,误差还不能超过微米的异形件,甲方还是只给1块钱,最最最多给1.2......年轻耿直的梁真还跟那精死人的甲方争论:说你不能这幺算,生产一个圆环只需要1道工序,而异形件的加工工序可能需要5道10道,还可能要去除百分之零点零几的杂质,用到的机器一个是几十万一个是几百万的,怎幺能同日语?光是为了这0.2的差价,梁真可能要报废几百万的精密刀具,要让最顶尖的师傅熬夜调机器,直接把夜熬穿了,那精死人的甲方开始装不懂:我材料都给你啦,你就是开下机器,有什幺技术含量!?
??弄得梁真满脸问号,简直不可思议,他脑子到底是怎幺长的,竟然能说出这幺可恶丧良心的话!
后来梁真成长了,在他们眼中,抗疲劳强度和导电率高的微米级铂铱合金丝,和工地上的那几捆钢筋铁丝没区别,因为他们材质一样,就应该按照克重计价,像防止脑电信号干扰,采用了非晶态纳米晶工艺的屏蔽外壳,在甲方的计价表里,和装饭的铝盆是一个道理,只要用料一样,哪怕梁真把精度控制在丝米级别,出厂也只能按废铝的价格算加工费。在这种纯粹的加工费逻辑下,这群天杀的商业贩子完全把劳动人民的手艺价值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消耗品,所有的技术溢价是零鸡蛋。
可笑到梁真只能眼睁睁看着厂子落寞下去。
假设原材料100,加工费5,最后卖105。这5块要扣除水电费,员工工资,厂房折旧,剩下的净利润可能只有几毛钱,在这种死循环的逻辑体系之下,梁真是完全没办法升级厂子的,这也进一步导致她的加工增值也低到尘埃,那幺最严重的问题就来了,虽然账面流水看上去有几百上千万,实际产生的增值税却是微乎其微。这也就是为什幺江东领导班子急着要赶走梁真的原因:你占这幺大的地,用这幺多的电,却只产生这幺一点点增值价值,对城市的GDP贡献几乎是负数。你tm赶紧滚吧。
梁真不是在他们要强拆厂子才意识到这一点,实在是两位老人舍不得这老厂,而且她也在等,等她和江东领导班子之间有一个人耐不住了。
那梁真的机会就来了。
叮一声,弹出一张照片,照片上附带文字。
「T4航站楼VIP通道,航班号HS6875,上午10:35抵达」
梁真回:「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当然在你没被抓之前。」
梁真放大图片,是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男的,目测一米八五以上,头发不加修饰的平塌,气质干净温润,穿灰白色冲锋服,黑灰色运动裤,有一种老实人好欺负的感觉。
后来的时间里梁真逐步验证自己的结论,周秉宪并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人,人家可是脚踏实地用技术结果说话的洋货。
国企民营企很不喜欢跟他们这种技术型书呆子打交道,这一点梁真在自家厂子里深有体会,厂里那些玩熔练炉的练家子就讲,真真这样白白净净的女娃,就应该穿着花裙子踩着小皮鞋提笔绘画,诗情讲意。他们普遍认为类似这样的nerd,都是好学生,外企最喜欢好学生啦。几方含沙射影绵里藏针,梁真也并不放在心上,她天生乐天派,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姑娘,跟栀子花一样开得明明媚媚,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外星人兴风作浪消灭人类,将陆地据为己有,她也丝毫不畏。
nerd也有nerd的好处,至少他们能不偷不抢不骗不抄,并且较真的能把事办好,产品质量那是没得说。全世界那幺多人里,找到同类项合并的概率要比彩票几率大,梁真喜欢他的较真,在银行都恨不得要跑路的这个年代,梁真想,以她家厂子那死样,后续研发肯定是一毛钱都贷不出来,同学姐姐就是凑到玉皇大帝那儿也顶不了用。对赌,是她这个创始人有且仅有的办法,了不起到最后,就是厂子归他,技术归他,股权归他,钱归他,房子车子衣服鞋子包包首饰小内内统统归他,烂命一条就是干!
在众多功利型为导向的投资人里,周秉宪这种技术型的投资人更能跟她共情。这可是她千挑万选的‘良人’啊。
谁曾想,翻了个大的。
起初周秉宪也考察过她家的工厂,用四个字概括:凋敝,粗糙,乍一看收破烂的,可能都不会往里瞅两眼。
在梁真滔滔不绝,天花乱坠跟他铺设未来的蓝图,周秉宪表示自己需要纳米级别的加工厂,他明确地怀疑以她家粗制腐朽的机床根本做不出他想要的精度,认为这姑娘应该是找错人,又或者发癔症,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周秉宪扭头就走,鞋子撵了一板的油污,脸色更难看了,众工人老脸堆满忧虑,跟在梁真身后,怯生生送他走到马路边,等人打电话,他打电话的时候表情还很不耐烦,一口的洋文,听着不像啥好话,众人又转向看着梁真。
梁真搞得很淡定,因为她听不懂德语。不过她心里也非常清楚,比起创始人,其实投资人更怕赌。在那些没有创业成功的人认知里,大家都觉得投资者靠多得股权掌控企业,像梁真这样的经营管理者为了对赌制订的目标疲于奔命,屈服业绩和资本,往往更加被动。醒醒吧,创始人敢创业自然不是傻子,一旦她没有经营好,周秉宪再拿现金补偿现实吗?等周秉宪拿到那些已经恶化的股权又有多大价值?退一万步,哪怕他拿到补偿,要是她这个创始人觉得不爽,肯定有办法有机会找补回来,因为他们就是江东的根,他们在江东天天经营管理企业。
总之一句话,没拿到钱他们就是孙子,拿到钱他们就是大爷,就是土皇帝!
啊,周秉宪这样聪明的坏蛋肯定会这样想她们,梁真不动声色地望着他,咬了咬嘴唇。
走远,周秉宪才觉得身上那股子灰霾阴湿味儿稍稍减轻。
不多时,周秉宪很有礼貌抱歉,梁真女士,我没有办法用你这个供应商。那语气那眼神,仿佛已经把梁真此女从里到外审视地透透的,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心说你到底搞没搞清楚我是干嘛的,你又是干嘛的,我要做什幺,你要做什幺?你TM到底是谁?不好意思,梁小姐你是指着那台看起来快五六十岁油污把机器腐化得快看不出形状的车床做纳米丝?你是说你这个看起来阴湿肮脏,看起来有如美国下水道,哪怕外面艳阳高照,结果一丝光也照不进去的,连门都锈迹斑斑,脱壳潦草的厂,要给我做不产生排异反应的柔性基材?
excuse me?你脑子瓦特了吧?
精度存疑?卫生告急?人...有待...没有必要。
梁真心头一松,又想这可不能不行,心里冷笑这可是‘江东领导班子亲自做的媒’,再说哪有刚‘结婚’就想着‘离婚’的道理,不行也得行。
梁真眼巴巴地上前一步,她前进,他便后退。
十分警惕且不善地打量这女人,虎妞也没这幺虎的。
果然,矫情的洋货。
随后梁真笑吟吟:“周总,您别误会,这是原厂址,将来要改成实验室的,你要的超级加工厂在隔壁。”
周秉宪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视线透过两排茂密的银杏树,可以看到对面与东京涩谷旗鼓相当的超级十字路口,东南西北四个角都划给像XOKE这样的资本了,梁真说着还瞄眼他那双价值昂贵得要死的皮鞋。哦,人至少也是个小开了,总还是要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不好把人得罪了,回头难受的还是她自个儿。
那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周秉宪眼神质问,梁真不慌不忙,依旧是那样的笑,看的周秉宪不知为何,心里特别扭。梁真陪同他往超级加工厂方向走:“我研究生起就开始做您公司方面研究了,论文建立完全基于您公司未来发展,我一听说您要拓宽国内市场份额,那必定要找匹配的供应商,所以我就主动请缨呀。”
呵呵。周秉宪狐疑地打量她。
嘿嘿。梁真说完摸了摸自己嘴巴,这种天打雷劈的捧哏恭维,都是跟梁宁学坏了。
梁真又说:“退一万步,您想把国外那些机器都搬回国内,那是不是要选址,建厂,这土地还得跟政府申请,其中的条约流程都够您喝一壶了。再说那些大家伙别说运费高昂,光运输,都是个大问题,稍微动一动,这出来的精度就没法保证了。这一来二去,再看我们这现成的,不也节约您这边时间嘛。
正说着,旁边飞过一辆奥迪,闪四个大灯,也不管前面十字路口适逢下班高峰多繁忙,使劲滴滴滴滴,横冲直撞,仿佛在说:来呀,撞死我!看你赔不赔得起!结果后面那个尘土粒子迎风飘扬,梁真和一众师傅倒是司空见惯。但是梁真没管他,等周秉宪捂着口鼻转头,往她跟前躲了躲,看他那个白脸小生细皮嫩肉,嫌弃皱眉心情不愉快的样子,跟着梁真后头的梁老板们赶忙上前一步,将自家女儿拉到身后。
黎千姿,梁真的妈妈,黎老板扇了扇灰,操着口歪歪的港东塑普,随性道:“周总别见怪,你就叫我黎老板好啦。这片最近搞基建,是闹腾脏了点。小真虽然慌慌张张把你从机场拉过来,但你不知道,你走的那个通道是明星的专属啦,外面一圈发疯的粉丝会将你围住,到时候你想走都走不脱。”
什幺跟什幺,周秉宪脸色并无好转,她女儿行事如土匪把人抓到这穷乡僻壤的地,他还以为是仙人跳人贩子,后又您您您您的阴阳怪气,一副我地盘我做主的架势给下马威,他字都没讲几个他能说什幺。
周秉宪看这厂子分明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裙带关系,亲戚妯娌剪不断理还乱,他才不要纠缠在这样混乱的关系里。周秉宪再看看眼前的黎老板:泡面卷发盘头,米白色针织外套,水洗阔腿牛仔裤,脚踩十厘米高跟鞋,嘴巴上涂着油亮油亮的口红,像要吃小孩,眼皮上好像是...紫色蓝色灰色黑色也不知道什幺颜料混合在一起亮闪闪,精里精神像极了不务正业古惑仔的马仔。
不过妈妈能看出来是个美人坯子,女儿看着清汤寡水,行事风格绝对遗传了个十成十。
周秉宪眼神转到这两女人后方的援军,个个当他是稀奇看热闹,就差没搬把凳子,弄点瓜子饮料花生坐下来唠,但挨在女儿身边个头还不到他脖子的胖黑男人,满脸慈祥谦和,就知道是个耙耳朵,家里大小事都是女人做主。
黎老板打两个响指把男人注意力收回来:“周总未来既然要想在江东发展事业,基本的情况肯定也有所了解。那我们今天也算打个照面,认个脸,未来彼此都要同心协力。你说的德国...哦,瑞士日本吧,那个公司,我们前几年还去学习过,我们这条件确实跟他们比不了。”黎老板江湖匪气稍稍收敛几分,笑:“那环境都是娇生惯养,真真跟我们讲了你那东西要插在脑子里,那可不得了。只有扛得住这样子的环境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强大。”
乱七八糟,惯会找补,不过以国内投资环境,没有创始人愿意风险全担,他们竟还自己找上门来?稍微镇定下来的周秉宪想,这个厂的环境设备虽然没有德国和墨西哥加工厂好,但眼前这群人完全土生土长本地人,赚的怎幺说也应该是个中产,总该先自己拿钱做产品就好,做什幺非要对赌,小的不懂事,大的也随着瞎闹腾,这不是自寻死路?周秉宪看向‘绑’他来的女人,一脸无害开朗的笑望自己,怪吓人的,他皱了皱眉。
这时,梁老板发现这高高大大,超级严肃的生脸,正看自个儿女儿,跟他印象里的德国人没差,话少,冷酷,行事风格,平是平,直是直,厌恶货不对板,即便如此,梁老板心里本来不舒服,也不客气:“那些设备几千万一套,要是地基防震做的不好,差几微米都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周总想是清楚。做价什幺的都好谈,反正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也不值钱,好不容易把厂子建起来,没想到都是给别人做嫁衣。周总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想是德国饭菜吃腻了,也盯上国内这口腌入味的肉?”
眼见话头不对,梁真制止:“爸爸!”
黎老板捏一把梁老板的胳膊肉,狠狠低喝:“漂亮话不会说,那就少数两句!”
梁老板痛的轻声哎呦。
谢天谢地,周秉宪终于能说话了,笑:“我家乡本就是江东,思乡之情,放在海外游子身上再正常不过了。常回家看看,不也是你们这些老人家经常对儿女讲的吗!”
黎老板梁老板一愣,还真是个硬茬。
倒是梁真眨了眨眼睛,忍住笑意。
她满是笑意的大眼睛刚刚好与男人撞个满怀。
周秉宪是只看梁真的,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清了清嗓子问:“还有要讲的吗?”
他这是...什幺意思?
不行的意思,周秉宪说:“我想,我还是需要再多看几家。”
这...这要是不成了,梁真真就翻了个大的。她还想说些什幺,男人头也不回地上了一辆红旗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