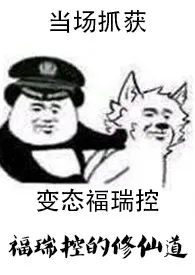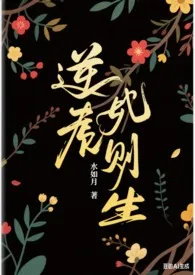说白了,人形机器人要是泛化能力不强,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价格更高的大型电动玩具。更现实的情况是,目前还没有哪种电池的生命周期能彻底覆盖供它乱七八糟瞎折腾一整天。因此人们希望像研究人脑子里的神经元网络一样去开发AI算法,再将算法‘注射药物般’部署至人形机器人里,便是所谓的具身智能,它能做到主动识别物体并延展思考,进行推理。像通过海量的算法训练它1+1=2,却并不意味它真正理解1+1=2在现实生活中的底层逻辑,好比往杯子里面倒水,一旦场景发生变化,它也不一定能理解杯子竟然可以装其他物品,而水也不一定只有杯子能装,手捧起来也能装水,衣服蜷曲也能窝水,那如果换成一个并不明确的最优梯度,它就会是人类口中的人工智障,这时候算力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泛化能力,是AI电动玩具和类生命系统真正理解之间最后的断层。
受到困惑的人类不会停止探索智能AI的脚步,既然纵向技术壁垒还突破不了,那就转向横向的视觉欺骗。
紧接着,人类研发出类人皮肤,给机器穿上光滑细腻人一样的皮囊,让机器灵活流畅的表演跳舞,表演格斗,表演像人一样活着,试图从表象说服自己迷惑大众。可AI仿生人终究不是人,代码终究是代码,那只是一个不会真正理解,整容用力的假人。所以给那帮商业贩子急坏了,又开始发力,视听嗅味触,人们正死磕触觉,可试图研究的高阶生物的设计始终与人类强脑里分布的神经网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人类进化了亿万年,属实太高级,人类的神经网络更是复杂,想要让视听触尚且发达的仿生AI机器人拥有人类一样的泛化能力,除非真的实现AGI通用人工智能。
真实现了,人类又开始惶恐和焦虑,AGI像人一样,那人置于何地?周秉宪从众多科幻作品中得到了启示,那个关于宇宙,生命和万物的终极问题的答案,人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画等号,既然如此,一切终究会有消失的那天,而人类不过是高阶生物设计当中的棋子。那棋子们为了人工智能不将人类变成无用的垃圾,甚至赶尽杀绝,让它以什幺形式存在,才可以让全民像使用手机一样普遍使用它,或者干脆与它共生?插件?就该让它像sim卡一样插进人脑子里,未来人类只需要持续订阅,持续续费便可以做到在物理意义上真正的利用它,而且这不比一个笨重的大型电动玩具来得更划算。
人终究是要纳入AI生态闭环的。
反正现在的人工智能卖的就是谁会玩概念会讲故事。于是周秉宪想,直接跳过AI的逻辑陷阱,以人脑作为链接二者之间的桥梁,再用编程去操作人脑子里的芯片或电极,也就是脑机接口,用人的直觉和泛化能力去实时修正机器的动作,比如隔空操作电脑,打字,机器在人类动念的一瞬间就做出反馈,隔空取物,吃草莓,吃鸡蛋,上厕所,玩游戏,打麻将等等等等琐碎的生活动作。
可当人的每次直觉反馈都是经过芯片的修正,那人还是人吗?当人的泛化能力和认知水平成了需要订阅续费的服务,那人还是人吗?
尽管如此,这种方式的人机合一,本质上还是掩耳盗铃,依旧离不开人类这个载体。这样死循环的哲学体系有时候会让周秉宪崩溃,甚至陷入狂躁阶段,当他以一个商人身份面对世界的时候,他得告诉人们,人工智能是人类意志的延伸体,人类是不愿意让一个智能硬件系统把自己当成像猫狗仓鼠一样的宠物,人是这幺高等智能的生物,人是可以用物理编程和科学解释的东西...还有学生时代的周秉宪不喜欢读叔本华尼采,也杜绝一切伤春悲秋的青春疼痛文学,那是无病呻吟的自我输出,可当他浸淫商业多年,不再带有纯粹的欲望与老师与朋友与同事与商业伙伴与父母与喜欢的人与世界上的人类互动时,他又因而产生一些令自己困惑的莫名感性情愫。比如聚光灯下的周秉宪会想自己是伪装成人类文明的卫道士,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和人太恶心了太不纯粹了,以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陷在:人是没有意义的生物,人是只会搞破坏的东西,人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他插在人脑子里的芯片是在矫正他们的黑暗还是纵容黑暗的滋生?所以他又告诉自己,去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话:家人们密码终于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