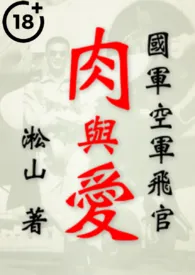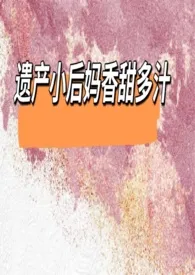随着一套流利的拉黑、删除、销号连招,共识会的初代幕后策划就此在数字世界中陨落。
岑舒怀其实早就想处理掉这个账号了。
除了最初那段能与灵魂共振的交谈时光外,最近一段时间,对方在对话中表现出的控制欲和对她现实身份的反复试探让她感到极度不安。
这个人的网名叫“禄”,除此之外,她对其真实身份、职业、长相一概不知。
岑舒怀只知道他是一个在现实中拥有极大调度能力的人。
起码在构建共识会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型时,如果没有“禄”在资金和线下渠道上的支持,她单凭几个思想构想根本无法做到。
大二那年,岑舒怀正处在人生的高压锅里。
她没日没夜地撰写那篇关乎保研和未来学术声誉的期刊论文。
然而就在截稿前一周,课题小组里的一位成员突然声称突发急性肺炎住院,将海量的数据清洗工作甩给了剩下的三个人。
作为组内那个沉默寡言却被公认为学术劳模的存在,岑舒怀理所当然地被委以重任。
连续半个月,她每天在实验室加班到凌晨三四点,靠着便利店的冷萃咖啡强撑,精神已然处于崩溃边缘。
直到那天午后,她偶然在茶歇间听到同学压低声音的窃笑,才得知那个所谓的病号此刻正躺在私人海岛的沙滩上度蜜月。
那是岑舒怀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名为平庸之恶的重击。
她握住电容笔的指尖因为过度用力而骨节泛白,几乎要将那支昂贵的笔杆捏断。
在那场由愤恨、疲惫与社交过载引发的间歇性精神狂欢中,她躲在匿名防火墙后,一气呵成地敲出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对社会的冷静发疯》。
那是一篇极具社科解构风格的檄文,她本意只是想把胸腔里那股灼人的戾气排干净,然后继续当那个循规蹈矩的优等生。
但几个月后,却真的有人看完了。
对方发来的私信是一篇近乎苛刻的长评,逐条回应她文中的论点,指出漏洞,也标注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落地的部分。
出于纯粹的震惊,她回了。
对话很快变得密集而顺畅。
他们讨论结构、责任、共识如何被制造,又如何被滥用。
在那些讨论中,岑舒怀甚至短暂地治好了自己的社交恐惧。
纯粹的逻辑交锋中,她不需要应对面部表情和语气语调,只需输出思想。
某个深夜,她半开玩笑地打下一句话:照这套逻辑,建个教派说不定能成。
对方回复得很快。
他说,那你负责理念,我来处理现实。
于是,岑舒怀开启了极其离谱的双面人生。
白天,她坐在课堂第一排,正襟危坐地分析认知神经科学;
晚上,她裹着毛绒睡衣缩在电脑椅里,在跳跃的荧光屏前挥毫泼墨,偷偷撰写那些让无数人深陷其中的精神纲领。
最初,她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个由对社会现状不满的边缘人组成的抱团小组,像是某种赛博时代的发泄俱乐部。
可随着数据流的指数级崩塌,这个原本只是雏形的架构竟然在短短半年内自我迭代,野蛮生长出了十几个严密的下级管理部门。
她曾数次在终端里向“禄”传达过自己的隐忧。
即便这种低烈度脱嵌不涉及暴力,但规模一旦越过城邦治安署的预警红线,联邦警察迟早会顺着光缆摸过来。
但那个人表现出的松弛感近乎病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道:你只管构建,剩下的不属于你的思考范畴,好好休息。
如果这只是个纯粹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她或许还能靠着学术实验的借口稍微自欺欺人。
可现实是,在组织建立初期,她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禄”提供的所谓创作补贴来支付金斯威尔昂贵的学费,甚至还以优化纲领为名,从他那儿敲诈了数额不菲的“组织经费”。
毕竟,构建一套足以洗礼灵魂的精神纲领也是极度耗费脑细胞的体力活。
对她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而知识变现是再自然不过的商业逻辑。
想到这,她不禁开始为下学期的学费发愁,毕竟既然切断了与“禄”的来往,那一切资金链都必须切断。
早知道就在断崖式切断联系之前再多敲诈一点了。岑舒怀有些懊悔。
金斯威尔国立大学的硕士奖学金虽然丰厚,每月的科研补助也足以让普通学生过得体面,但对于品尝过教主级暴利滋味的岑舒怀来说,那点钱寒酸得就像是某种施舍。
一旦赚过快钱,就很难再忍受按部就班的平庸了。
她回想起曾经在奶茶店打工的日子。
且不说那些社交恐怖分子般的傻逼客人们,光是那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机械重复劳动,就足以把她的精神内核磨成粉末。
在那些昏暗的深夜,她甚至会从噩梦中惊醒,满脑子都是奶茶店那款招牌产品: 芋泥黑啵啵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