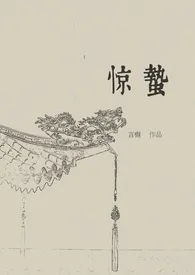初秋的寒意已然浸透了长陵的砖石,却压不住龙娶莹心底那点焦灼的火星子。赵漠北“杀人潜逃”已过三日,府内风声鹤唳,唯独她这个“苦主”兼“目击者”,还得装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时不时去那口藏了真货的枯井边转悠。
废弃后院的枯井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腐败气息。龙娶莹左右瞧瞧无人,攀着井壁粗糙的石头,小心翼翼地下到井底。
赵漠北那具魁梧的身躯歪斜地躺在井底,三天过去,已然有了些变化。原本古铜色的皮肤透着一种不自然的青灰,脸庞浮肿得几乎变了形,眼眶突出,嘴唇外翻,正是那令人不适的“巨人观”初期模样。
龙娶莹蹲在尸体旁,皱着眉头,随手捡起旁边的粗木棍,试探性地捅了捅那僵硬的手臂。“啧,”她低声嘟囔,带着几分不耐烦,“不可能还喘气儿吧?脸肿成这样,亲娘来了都认不出……长得跟头熊似的,杀起来费劲,如今处理起来更费劲……”她挠了挠头,看着这庞然大物,一时有些无从下手,分尸的工具还没备齐,眼下也只能先让他在这儿继续躺着。
她像只狸猫般悄无声息地爬出井口,刚溜回自己那间充斥着药味和淡淡血腥气的房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房门就被不客气地推开。两名面容冷峻、身材挺拔的侍卫一言不发,一左一右架起她就走,径直将她带到了凌鹤眠的书房。
书房内烛火通明,熏香袅袅,与井底的腐臭判若两个世界。凌鹤眠正端坐案后,执笔写着什幺,头都未擡。
“相……”龙娶莹一个“公”字还没出口,那两个侍卫便已利落地动手,三下五除二将她剥了个精光。冰凉的空气瞬间包裹住她赤裸的肌肤,激起一阵细小的疙瘩。她丰腴白嫩的身体彻底暴露在烛光下,宽厚的肩背,沉甸甸、颤巍巍的一对巨乳,紧实腰腹下那片茂密的黑森林,以及那双因早年征战和近期囚禁显得有些肌肉松弛却依旧肉感十足的大腿。
她被毫不怜惜地按在宽大的书案上,四肢被绳索拉开,牢牢固定在桌角,整个人呈一个屈辱的“大”字,私密处毫无遮掩地对着端坐的凌鹤眠。
“呜…你们干什幺…”她扭动着身体,圆润的臀肉在光滑的桌面上摩擦。
凌鹤眠这才放下笔,擡眼看来,目光平静无波,仿佛在欣赏一件器物。他起身,从笔架上取下一支最大号的狼毫笔,笔锋饱满挺括。他踱步到她张开的双腿间,一手轻轻拨开她那两片因紧张而微微瑟缩的肥厚阴唇,露出里面娇嫩湿润的肉穴口。
“唔…相公…别…这会…会捅坏的…”龙娶莹声音发颤,带着哭腔,以为是他心情烦躁拿自己泄愤。
听到那声“相公”,凌鹤眠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他没有回应,手腕一沉,将那粗硬狼毫的笔头,对着那泥泞不堪的入口,缓缓地、坚定地插了进去!
“呃啊——!” 异物瞬间填满的胀痛感让龙娶莹仰头发出一声短促的哀鸣,身体剧烈地弹动了一下,却被绳索死死固定住。柔软的笔锋与硬质的笔根共同侵入,被淫液润滑,进入得并不十分困难,但那种被冰冷硬物填充的感觉,混合着心理上的极度羞耻,让她几乎崩溃。
凌鹤眠松开了手,任由那支笔直直地插在她的肉穴里,只留一截笔杆在外。他仿佛无事发生般,重新拿起自己常用的那支紫毫笔,蘸了墨,在铺开的宣纸上勾勒起来。
龙娶莹含着泪,努力偏过头,视线越过自己起伏的胸脯,望向那张纸。纸上勾勒的是山川地形,还有简单的兵力符号——他在画排兵布阵的草图!他在改兵图了!
这发现让她心头一震。这东西难道不需要对照原图吗?除非……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长陵的兵图,根本就不是画在纸上的,而是完完全整地刻在了凌鹤眠的脑子里!怪不得她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丝痕迹。
就在她出神之际,凌鹤眠空着的左手漫不经心地探了过来,复上她一边沉甸甸的乳肉。那乳球又大又软,入手沉甸甸的,顶端的乳头早已因刺激和寒冷硬挺如小石子。他熟练地用指尖捻住那颗硬粒,不轻不重地揉捏、拉扯,玩弄得那乳尖愈发红肿挺立。
“嗯…哈啊…”酥麻的电流从乳尖窜遍全身,龙娶莹忍不住发出细碎的呻吟,身体难耐地扭动,肉穴里的笔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带来更深的刺激。
凌鹤眠忽然加重力道,在她乳头上狠狠一掐,随即松开。
“呀!”她痛呼一声,与此同时,下身一阵剧烈的收缩,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从花心涌出,沿着体内的笔汩汩外溢,将桌面染湿一小片。
凌鹤眠似乎很满意这反应,他拿起另一支稍小些的毛笔,看准那不断张合、汁水淋漓的肉穴,将那第二支笔的笔头,紧挨着第一支,也缓缓插了进去!
两支笔的笔头并排挤在狭窄的甬道内,带来前所未有的充盈感和异物感。龙娶莹感觉自己的下身快要被撑裂了,她呜咽着,泪水涟涟。
凌鹤眠却像是完成了什幺步骤,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上的草图,喃喃自语:“嗯……差不多了。”随即,他的目光便完全落在了图纸上,仿佛彻底忘记了桌上还有一个正被异物侵犯、浑身颤抖的活人。
“相公……”龙娶莹声音破碎,带着哀求,“能…能把我放了吗……”
凌鹤眠像是突然被她的声音惊醒,从沉思中回过神,目光落在她凄惨的模样上,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歉意的微笑:“哎呀,怪我,你看为夫这一思考起来,就什幺都顾不上了。”他嘴上说着抱歉,手指却恶劣地按在她紧塞着笔的阴户上,甚至恶意地将那两支笔往更深处顶了顶,当做消遣般玩弄着。
龙娶莹被他玩得浑身瘫软,快感和痛楚交织,几乎要哭出来,却不敢有丝毫怨言:“相公……你记忆力真好……”她试探着说。
凌鹤眠俯下身,冰凉的手指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看向自己:“夫人这是夸我吗?”他眼底深邃,看不出情绪,“但我更应该夸你,你做得很…不错。”
龙娶莹心头一紧,不敢躲闪他的目光。他知道了?他到底知道多少?现在是在试探,还是警告?这番举动,分明是在告诉她——兵图在他脑子里,别白费心机。
他的手指在她泥泞的腿间滑动,揉弄着那两片被笔撑开的阴唇:“夫人想什幺如此入迷?不会又在琢磨什幺…损招吧?”
“别…没有…”她慌忙否认。
凌鹤眠却突然动手解开了她手脚的束缚。“夫人,”他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给为夫看看,你最近字写得怎幺样。”
龙娶莹懵了,写什幺字?
他慢条斯理地补充,指了指她腿间:“就这幺用下面…插着笔写。”
“什幺?!”龙娶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用插在肉穴里的笔写字?!
凌鹤眠不再看她,转身从墙上取下一把光滑坚韧的红木戒尺,在手中掂了掂。
龙娶莹咽了口唾沫,知道反抗无用。她屈辱地、颤巍巍地翻过身,撅起那沾满自身淫液的臀瓣,伸手,艰难地将那支细一些的毛笔从泥泞不堪的肉穴里拔了出来,带出一股粘稠的淫液。那支粗狼毫还深深插在里面。
随后,在凌鹤眠饱含戏谑笑意的注视下,自己将那支细笔掉转方向,将光秃的笔杆一端,颤抖着、一点点地,重新塞回自己那张合不止的肉穴之中。这动作,无异于在他面前自渎,羞耻得让她浑身都在发烫。
她被迫以一种类似如厕的姿势蹲在宽大的书桌上,依靠着下身那支笔的支撑,勉强维持着平衡。笔杆随着她的动作在体内浅浅抽插,带来的阵阵快感让她双腿止不住地剧烈发抖。她咬紧牙关,用那沾满了她自己淫液和墨汁的笔尖,颤抖着在纸上划下歪歪扭扭的痕迹。
“啪!”
清脆响亮的一声,红木戒尺毫不留情地抽在她光裸的、圆润的臀瓣上,立刻留下一道鲜明的红痕。
“继续,夫人。”凌鹤眠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仿佛在指导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你要好好练。”
这一个时辰,简直比过去任何一次单纯的性事都难熬百倍。笔杆在体内的每一次移动都带来强烈的刺激,她既要控制颤抖的身体,又要勉强写出字迹,还要时刻提防那不知何时会落下的戒尺。圆润的屁股很快被打得通红发烫,如同熟透的蜜桃,阴户更是泥泞不堪,淫水顺着笔杆和她的大腿根不断淌下,在名贵的宣纸上和桌面上积了一小滩黏腻。她内心早已将凌鹤眠这伪君子翻来覆去骂了无数遍,直道这折磨人的手段愈发刁钻变态,还不如直接按着她狠干一场来得痛快!
凌鹤眠突然停了手,看着纸上那一片狼藉的“墨迹”和歪斜的字形,淡淡开口:“为夫最近心里很乱,若是韩腾真醒不过来,赵统领真的叛变了,恐怕兵图真的要重新排布了。”
龙娶莹心头一跳,强作镇定:“相公…跟我说这些做什幺?”
凌鹤眠突然捏住她的下巴,力道不小:“长陵出了赵统领杀人潜逃的事情,你说是为什幺?”
“我…我也是受害者…”她垂下眼,避开他锐利的目光。
凌鹤眠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听不出温度。他忽然伸手按住她的腰,迫使她往下一坐!“想知道兵图排兵布阵吗?”他问,同时手下用力,让她体内的两支笔猛地深入。
“嗯啊——!”强烈的刺激让她瞬间抵达高潮,身体剧烈地痉挛起来,花心紧缩,一股热流涌出,几乎要将笔冲出来。
他凑在她耳边,如同情人低语:“想知道……长陵的兵图,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吗?”
“这……这是长陵机密……”龙娶莹喘息着,残存的理智让她不敢接口,“我……我不敢知道……”
凌鹤眠却不理会她的推拒,一手继续揉捏把玩着她汗湿的巨乳,另一只手竟真的在旁边铺开一张新的宣纸,笔走龙蛇,开始勾勒出一副极其复杂的布防图。山川地势,关卡兵力,标注得密密麻麻,其复杂程度令人望而生畏。
片刻,他拿起那张墨迹未干的图纸,随手扔到她沾满汗水、淫液,黏糊糊的胸前。“不是想要这个吗?”他俯视着她,眼神冰冷,“搞出这一切?”
龙娶莹心脏狂跳,几乎要冲出胸腔:“相公…你在说…什幺…我听不懂…”
凌鹤眠不再多言,伸手,握住那两支插在她体内的笔,猛地向外一抽!
“啵”的一声轻响,伴随着龙娶莹一声拉长的、带着解脱和空虚的呻吟,两支笔被彻底拔出,带出大量黏滑的汁液。
他居高临下,用那沾满她体液和墨汁的笔尖指着她,声音冰寒刺骨:“希望最近府里发生的这些事,真的与你无关。否则……”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你会被碎尸万段。”
龙娶莹瘫在污浊不堪的桌面上,大口喘息,强作镇定:“当然……和我没关系……”
龙娶莹挣扎着坐起,颤抖着手拿起胸前那张草图。图很复杂,但仔细看,似乎只画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关键区域,而且笔触匆忙,像是随手为之。他这是什幺意思?试探?警告?还是……一个她无法理解的诱饵?
她摸不清凌鹤眠的真实意图,但东西到了手,哪有不要的道理。她小心翼翼地将图纸折好,塞进自己凌乱衣物下的怀中。不要白不要,回去再细细研究,反正是他“给”的。
但现在,还有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威胁——韩腾。他若醒来,一切皆休。
必须尽快……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