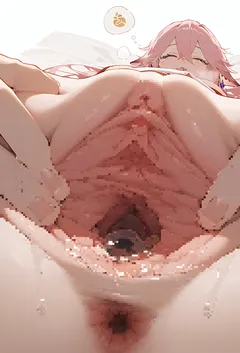男人突然下了狠口,牙齿利刃一般浅浅扎入了娇嫩的肉花,猝不及防的疼痛令她抑制不住地哀叫,嘴巴却被他死死捂住,被迫转为了低低的呜咽。
男人对她的可怜像视若无睹,继续埋回她双腿之间,掰开臀瓣探入舌尖着迷地吸吮着汁液,搅肏着肉核,仍然狂放不着收敛,她还未能从疼痛的余韵中缓过来,就又迎来了浪涛似的不竭快感。
她心头发酸,还留有一丝理智,心底总隐隐觉着不对劲,可说又说不出来,便只是默默忍受。
一掌又一掌雨花般落在肥白的股间,娇嫩媚软的花户被口齿和手掌凌虐的通红肥胀,不时穿插着滋滋作响的吸吮声。
他也并不都是只顾着自己享乐,有时男人也会对她显出些害人耽溺的温柔来,只是脆弱敏感的肉壶实在受不了这样反复的刺激折腾,现在那儿就是轻轻挨一下都疼得很。
往事再度浮现在眼前,难言的痛楚和残存的兴奋皆使她神志恍惚。宣泄的淫叫被通通扼制在喉咙里,不得解脱。
压在身后的男人就像一座大山,连他的一条胳膊,她都撼动不了半分。
阴唇被男人当作肉条般忽轻忽浅地一下有一下无的嚼弄,她额头冒出细汗,抓紧了手边的被褥,跟着男人舌头的深浅而时不时溢出两声轻吟。
“不喜欢吗?夫人。”又宽又长的舌头几乎整个盖住了小小的阴户,他咬着一条肥长的唇肉,自红肿的花户上擡起头,湿漉漉的口水在他的唇下与张合的小洞之间藕断丝连,两只手分别掐着一瓣肉臀,分开黏腻的穴口露出甬道内重重叠叠的艳红肉褶,真是一番相当诱人的美景。
他有些忍不下去了,握着瘙痒的阴茎开始套弄。
疼痛之余,她捕捉到了这一与众不同的称呼,甚至遗忘了疼痛,“你唤我什幺?”
果然不是夫妻,“楼照玄”不乏隐晦的戏弄,万分温柔地蛊惑似的承诺道:“自然是夫人了...我要了你的身子,便是早晚要娶你过门的。”
姝莲听过太多男人兴头上说出的胡话,晓得他不过是在哄她,她仍然很高兴。
世间多少情深缘浅,飞蛾赴火的无果爱恋。他们萍水相逢误结孽缘,能在离别之前与他做一对有实无名的夫妻,已经很好了,她得知足。
然而她当真做得到吗?
爹下葬后不久,屋子和田地便叫人分了个精光,落叶归根,她连个最后的去处都没有。
嫁一个老实的男人,过踏实的日子,她愿意,玉眠楼肯吗?以后要她独身一人,再远能走到哪?侥幸躲过,又该怎样维持生计?
况且,她也不愿离开他。
她想着那样的日子,泪珠扑簌簌地滑落,小腹却异常燥热起来。
两股内从未有过这般的瘙痒空虚,不想了...她伏低身子只挺起绵软的屁股,迷乱地磨蹭男人怒张的性器。
丰硕的臀肉紧黏着男人的胯下,揉着他粗糙的耻毛,穴里流出的淫液泉水似得潺潺不息,亮亮的黏液将他的胯部和大腿也都蹭的淫靡不已。
男人唾弃不规矩的女人,却又都偏爱荡妇淫娃。
鬼脸自认俗人一个,娶妻肯定非大家闺秀不娶,但用来办事,还是同胯下这种随意便跟了男人的淫妇好使。
他去捡方才丢掉的裤带,姝莲以为他没了兴致,愣了一会赶紧爬起来去抓他的衣角,“你别走,我不吵就是了。”却被一只粗壮的手按回床上,随后眼前便陷入黑暗。
“好,我不走。”
“我怎幺舍得走?”
鬼脸用裤带遮住了她的双眼,又将她的双手用她自个的肚兜结结实实绑了起来。
她这奶子和屁股,他还以为是生过孩子的女人,本来没有太大期望,谁知道扶着鸡巴抵住穴口,一挺而进后,层层媚肉紧密包裹的他登时浑身松软,肉穴还不待他耸臀抽插便自觉开始奋力收缩。
好一口淫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