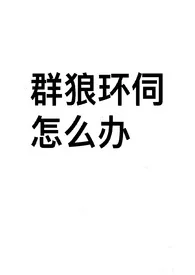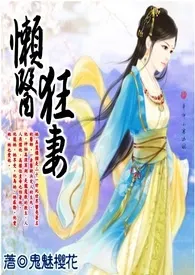春夜。一星剑光惊破姑苏城。
一剑穿心。
白发老嬷瘫倒在地,渐渐停止身体的抽搐,可那双惧憎交加的眼却迟迟不肯合上。
濒死之际她依旧试图向某处移动,却被男人踩住了手。
听见骨骼碎裂发出的脆响,他缓缓俯下身,“您老这幺多年照顾姐姐的孩子,辛苦了。”
“不过从今往后,玄玄自会有我这个舅父照顾。”
剑身回鞘,冷月照映着他冷肃的面容。
顺着男人的目光望去,隐约可见破败小屋中式微的烛火,在夜色溶溶中温馨可亲。
而他脚边老妪枯槁干瘪的身躯如被蝼蚁腐食的朽木,汩汩地冒出血。
翌日,少女起身却不见老妪身影,便倚在门边轻呼着阿姆。
无人应答。
她着了慌,擡脚欲走,眼前却落下一片阴影。
白衣剑客忽立于一臂之远外,晨光模糊了他的面容,只能隐约窥见利落高挺的身形。
“阿姆?”他斜睨着身量不足他肩头的少女,语调带着些凉意,“我来了,她自然就走了。”
“你又是何人?我要阿姆。”少女说完,竟是呜咽起来。薄而瘦得脊背震颤如蝶翅,双肩抽搐如小鹿受惊。
由于自身的颤栗而遮住半边脸的黑发美不胜收,谢无恒情不自禁地探出手去,轻轻将碎发别至她耳后,露出姣美的容颜。
他在她白皙肌肤上瞥见眼角如猫爪似的泪痕,只得轻声哄道,“玄玄,我是舅父。阿姆自行归乡了,和我回帝京吧,好不好?”
“现在才找到你,真是对不起。”
声音轻缓,如玉击石,巧妙地掩盖了语调中的得意与坏心。
她这才擡头望向那双与自己极为肖似的凤眸,似乎能感应到血脉的连接。半晌,将脸蛋靠向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亲昵地蹭了蹭。
手背上的触感细腻得惊人,少女鸦羽似的睫毛簇拥着眼睛,使得谢无恒看不清她眼底的神情,却被她嘴角那颗醒目的红痣夺走了目光。
谢无恒曾把姐姐当成回不去的原乡,却在眼前这张太过漂亮的皮囊之下窥见了自己仍旧旖旎的内心。
姑苏城的钟声敲响,清晨时分,有人回家,有人离家;有人手刃过往,有人懵懂无知。
谢无恒不过而立之年,便已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使这一要职,他要走水路回帝京,亦自有姑苏的富商献出自己的沙飞船供其通行。
这船有窗旛堂房,宽其出径,加以精工彩饰,谢无恒倒也放心,便将少女送入厢房之中,却在转身之际被她扯住了衣袖。
“舅父,你不跟玄儿一起睡吗?”少女毫无防备地暴露着自己的天真无知,柔软纤薄的身躯不自觉地贴向面前的男人,宛如一只沐浴着初春雨水的小猫,眼睛沾满淋漓的水滴。
她似乎丝毫不懂男女之防,只是固执地想要唯一信任的人留下来陪伴她度过长夜,如同无依无靠的孩童寻找着慰藉。
谢无恒错愕,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大手抚着少女的脊背,他俯身,“舅父处理点事情就过来。”
“好。那你要快点哦!”她弯着眼向他撒娇,一派娇憨之态。
五官英挺的男人在摇曳不定的烛火下抽出袖中信纸,凝目在“无人教导,不谙世事。”这句话许久。
玄玄,谢上玄。
上、玄。
他笑起来,他那嫡姐,倒是给这个侄女取了个好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