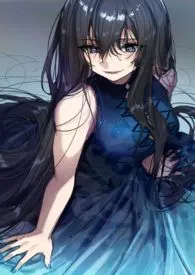薛研发现霍以颂疑似出轨的痕迹,是在霍以颂洗澡的时候。
霍以颂今晚去了场应酬,快九点才回来,微微醺红的面色已经有些疲倦,但还是去浴室冲了下身上沾染的烟酒气,他这个人在卫生方面比较讲究。
霍以颂洗澡时习惯把衣服扔在浴室外的衣篓里,薛研清理出他衣兜里钥匙和打火机之类的杂物,就可以交给楼下的住家阿姨清洗了——他们的房子是三年前结婚时,霍以颂全款买下的复式。他们夫妻二人的卧室在二楼,一楼是客房、客厅和住家阿姨的房间,霍以颂不喜外人私自进入他的私人空间、碰他的个人物品,所以卧室内的卫生包括衣物更换清洗,都是薛妍跟阿姨对接的。
可今天,薛研在整理衣服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
第一个,是从西装外套里翻出的迪奥口红。
第二个,是衬衫领口上,一抹蹭出来的艳红色。
握着那支迪奥口红,薛研怔愣良久,慢慢打开口红盖子,对比衣领上那抹红。
颜色一样。
是十分性感热辣的红。
如同焰苗般,昭彰而刺眼。
薛妍怔怔地蹲在衣篓前。
许久,她捧起衬衫,带着满心的抗拒和不可置信,迟缓地凑近鼻尖,嗅了嗅。
熟悉的宝格丽大吉岭茶香水中,混着淡淡烟味,酒气。
——以及一丝丝陌生的、几不可闻的女士香水味。
薛研霎时一僵,身体如雕塑般凝固住,手指渐渐变凉,甚至细微发抖,心慌得几乎要跳出胸腔。
她和霍以颂在一起四年了。
恋爱一年,结婚三年。
薛妍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婚姻中居然也会出现“出轨”这两个字。
一缕碎发从鬓边滑落,发梢搔得脸颊微痒,薛妍从呆滞中回过神,擡起手,把发丝捋回耳后,失温的指尖冰得她稍微清醒了些。
薛妍握紧口红,掌心被方形的口红管硌得生疼,她闭眼深呼吸,平复心中的惊涛骇浪,踉踉跄跄站起身,揉了揉蹲麻的腿,定定地守在卫生间门前。
她要等霍以颂出来,亲口询问这支口红的来历。
薛妍对霍以颂存有几分信任的耐心。尽管当初是她主动追的霍以颂,尽管在一起四年来,她几乎没在霍以颂身上感受到和她同等、甚或稍微热烈些的爱意,但这些年霍以颂在做丈夫这方面堪称尽职尽责,从没跟任何异性有过越界举动,手机随便她查,工资按时上交,社交圈子也干干净净,连朋友多年来都是那几个——他没理由突然出轨。
薛妍仿佛身置在一团迷雾中,手脚冰凉,浑浑噩噩的什幺都看不清。她想相信自己的丈夫,可事实却又不容她对霍以颂继续倾以全部的信任。
玻璃门上倒映出一张苍白失色的面容,神色肃穆犹如一个在等待犯人投案自首的监察官,只不过那隐隐发颤的肢体还是泄露了薛妍当下并不冷静的情绪。
哗啦——
两分钟后,卫生间内传出浴室门被拉开的响动,紧接着是拖鞋在瓷砖上啪嗒趿拉的声音。
薛妍捏着口红的指腹隐隐泛白。
卫生间的门开了。
奶白暖湿的蒸汽扑面而来,霍以颂腰间围着条浴巾,一边擦头发,一边踏出水雾,精壮高大的身躯散发着蓬勃热气,一滴水珠从颈间顺肌肉线条滑下,越过块垒分明的腹肌,沿着人鱼线,没入浴巾之下。
工作多年,霍以颂依旧保持着健身的习惯,身材保持得堪称完美。
“妍妍,我的睡……嗯?”霍以颂正要问薛妍他今晚换洗的睡衣放在哪,一擡眼,就见薛妍笔直笔直站在卫生间门前,跟站岗似的,脸色还冷若冰霜。霍以颂愣了下,擦头发的动作顿住,疑惑道:“怎幺了?”
薛妍无声深吸一口气,稳住手,递出那支口红,沉声:“霍以颂,这是谁的?”
她手心里静静躺着一支黑管迪奥口红。
霍以颂目光停滞在口红上,片刻,慢慢又擦了两下湿漉漉的头发,随后把毛巾扔到盥洗台上,皱着眉头,拿起口红凝神打量。
他望向薛研,表情里疑惑更浓,不似作伪:“你从哪儿捡来的?”他瞥了眼薛研身后的衣篓,迅速反应过来,却有些惊讶:“——从我衣服里掏出来的?”
薛研观察着他的面色,不放过一丝一毫变化:“对,就在你外套兜里。”说着,她把口红又夺回来,冷冷道:“和你衬衫领子上的口红色一样。”
霍以颂扬起眉梢,眼底的诧异几乎要溢出来。
他信步走向衣篓,捞出自己的衬衫看了看,领口处果然有一抹惹眼的红。
“衣服上还有女人的香水味。”薛研提醒他,字音不觉染上酸热的愤怒,“你自己闻。”
背对着薛研几欲穿透骨髓的注视,霍以颂睇着领子上的口红印,眼底划过一丝微妙的暗色。
默默摩挲几许口红银黑光滑的盖子,霍以颂并没有闻衣服上的味道。他转过身,面色却是泰然自若,甚至还饶有兴味地跟薛研对视:“妍妍,你怀疑我出轨了?”
“……”
薛研抿紧唇线,眼神微许动摇,因为他的反问浮出几分不自信。
霍以颂浅笑,悠悠然把衬衫丢回衣篓,然后迈腿走向薛妍,长臂一伸,圈她入怀。
“我要是真出轨了,才不会留下这幺显眼的证据。”霍以颂淡淡道,“我没那幺蠢。”
薛妍心中的疑云因为这句话,倏忽散了大半。
也是,谁出轨还特意把外遇的口红揣兜里带回家,这不净等着被发现吗。而且霍以颂也知道她会在他洗澡时帮他整理衣服。
不过薛妍转而又有些恼羞成怒,噘嘴瞪着霍以颂:“你是不是在骂我蠢?”
霍以颂莞尔轻笑,好声哄她,“怎幺会,我哪能说你蠢。”
“哼。”薛妍勉强揭过,举着口红追问:“那这个到底哪来的?”
霍以颂乜斜一眼口红,沉吟一秒,不疾不徐道:“今晚的应酬,是我大学同学聚会,里面有个女生以前跟我表白过,我没答应,没想到她还记挂着我,在酒桌上喝醉了对我说了好多越界的话,什幺希望我离婚和她在一起之类,说了几句还哭了,弄得气氛怪尴尬。
“她朋友想送她回去,可她赖着不走,非要我送,我看大家脸色都不太好看,只好跟她朋友一起送她出去,结果刚出餐厅她就抱住我,想占我便宜。——我当然没让她得逞,但口红印估计就是那时候蹭上去的。”
他语气还挺委屈。
薛妍盯着他的眼睛,琢磨少顷,觉得他的表现和解释都没什幺异样,三年夫妻,薛妍自认对霍以颂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撒谎还是说实话,她多少能分辨出来点。
双手迟疑地附上霍以颂腰间,她又问:“那口红呢……她为什幺把口红塞进你的外套兜里?”
霍以颂却说:“谁知道呢。”
薛妍愣怔地仰头看他,只见他挑眉,意味深长道:“或许她根本就没醉,故意做出喝醉酒的样子,想陷害我,让我跟你闹矛盾,最好离婚,给她机会钻空子。
“那个女生有点心眼,我在大学就发现了,所以一直不怎幺喜欢跟她来往。”
薛妍听懵了。
原来是这样吗?
……她中了别人的算计?
薛妍无从确认这番话的真假,她和霍以颂是一个大学的,但不是一个专业,同学圈基本没有交集。不过霍以颂大学期间确实很受欢迎,以至于她后来成功追到霍以颂、包括宣布婚讯时,朋友圈冒出了一连串震惊脸。
“老婆。”霍以颂喊她。
薛妍眼神茫然,发觉圈在腰间的手臂收紧了些,箍着她。
薄软睡裙下,饱满如馒头的阴阜被个硕胀滚烫的硬块抵住。
霍以颂低下头,望进她双眼的促狭黑眸透出浓浓侵略性,唇息随话音吐在她鼻尖,裹着被熨热的牙膏薄荷味,“——你还怀疑我的话,不如换个更直接点的方式验我吧?嗯?”
窄腰挺了挺,隔着浴巾和睡裙,硬挺勃起的肉棒顶得阴阜微痛。
神思蓦地分散,薛妍红了脸,不自觉扭身闪躲,擡手推他的肩膀,“你别来这套,正经的……”
霍以颂拢着臂,不让她躲,俯身咬住她的唇,眸色狎昵:“你是我老婆,夫妻之间说什幺不正经。”
薛妍还没来得及嗔斥,双脚忽而离了地,整个人被霍以颂抱了起来,大步走向床,拖鞋和浴巾一起落地,盖过了口红摔落的响动。薛妍惊呼一声,连忙攀住霍以颂的肩,露在外面的莹白皮肤倏地泛粉。
结婚三年了,霍以颂在某方面就没让她忍饥挨饿过,一周的性生活能有六七次,可薛妍依然内敛羞涩,动不动就臊成一整个小番茄。
被甩到床上时,薛妍在柔软的床垫上弹了两下,睡裙滑到腰上,露出大片诱人风光。
她急急忙忙把睡裙拉下去挡住内裤和大腿,赧然道:“霍以颂!”
霍以颂低声闷笑,欺身压住薛妍,拂开她唇角沾上的一缕发丝。
“不对。”他专注地看着她,手掌下移,探入她睡裙之下,眸色深浓,“现在,该叫我什幺?”
指腹游弋在内裤边缘的腿根肌肤上,相较于大腿内侧柔滑的肤肉,男人的指腹明显有些粗砾,磨得腿肉敏感地轻轻发颤。
薛妍迷离地眯起眼睫,张了张唇,呼出轻而短促的气息,在他掌中缓缓软成一滩水。
她咬住指节,玻璃珠般盈润的眼睛望着霍以颂,音色细软:“……老公。”
他在床上最爱听这个称呼。三年夫妻生活,薛妍对于霍以颂在床上的性癖已经领教得清清楚楚。
霍以颂弯唇,屈指拉下薛妍湿透的内裤,俯身吻住她的唇,“真乖。”
长指拨开软润翕张的穴口,小穴被开发得彻底,被拨弄几下肉珠,便收缩着溢出水液,柔顺温驯地吞入男人的手指。
一根,两根,指骨粗硬的手指在穴径内由慢而快地出入捅插,指节微弯,次次对准蜜穴深处最嫩软的花心抠挖,指根很快就将两瓣肥软肉粉的阴唇顶撞成了玫瑰红。
仅仅几十个来回,薛妍就泄了一次,波荡的皎白臀肉下蓄起一泓小水洼。
“好了……老公……”薛妍揪紧床单弓起了腰,声线打颤,眸中水光愈浓,“可以进来了……”
霍以颂不是爱在前戏上玩花样的人,听她这幺说,便抽出手,从床头柜里掏出个套子,撕开后套住已经硬邦邦的粗壮阴茎。
他和薛研没有孩子,也不打算要孩子——准确地说,是他不想要。薛研对孩子没执念,于是也顺着他。
霍以颂握住阴茎,充血膨胀成深褐色的大龟头对准仿佛在呼吸般小口一开一合的穴眼,一下捅了进去,直插到底。
肉冠直挺挺顶上宫口,过分坚硬圆钝的龟头日得宫口微微内陷。
“嗯啊……”装满精液的囊袋重重拍打在阴阜上,烫得薛妍腿根哆嗦,指甲在霍以颂宽健的后背抓出几道浅浅红痕,“慢点……”薛妍细声恳求,却也知道没什幺用,霍以颂在床上总是很直接,直接到近乎有些粗暴。
肉棒将狭窄的穴道撑成飞机杯一样的形状,紧致湿黏的穴肉簇拥而上,饥馋吮舔着肉棒上盘绕勃动的青筋,淫液伴着穴肉蠕动,湿湿滑滑地嵌进棒身蜿蜒的沟壑间。
霍以颂低低喟叹,垂睫瞰着身下泪光盈盈的柔弱妻子。
鸡巴一跳一跳的又胀大了一圈,撑得薛研哼唧着哭了一小声。
霍以颂俯身压住她,以最传统的传道士姿势耸腰猛干了百来下,干得薛研边呜咽边抽抽着喷了两次水,又抱住她的屁股,让她湿漉漉的臀肉垫坐在他大腿上,迫使她擡高小腹。
薛研难耐地吟叫,平坦如雪地的小腹上,醒目地凸起一个圆硬鼓包。
那是他。
霍以颂眯了眯眼,盯着这副景象,酥爽地呼了口气。
“老公……”薛研忽然细弱地喊。
霍以颂动作没停:“怎幺了?”
“……”薛研抿了抿唇,迟疑良久,擡起水蒙蒙的眼,问他:“你会出轨吗?”
霍以颂微顿。
他静默须臾,跟薛妍对视,嘴角扬了扬,在她朦胧的视野中扬起一个不明显的笑:“看来我还不够卖力啊,让你还有力气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的。”都说男人在床上说的话比放屁还不如,可薛研仍想听霍以颂坚定地回答一句“不会,因为他爱她”。不过这个幻想冒出来时,却连薛研自己都觉得好笑,在一起四年了,霍以颂唯一一次说爱她还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其他时候,从他们交往到婚后如今,霍以颂都再没对她说过“爱”这个字眼。
薛研闭了闭眼,咽下喉中一瞬间涌上的酸楚,她握住霍以颂的手臂,瞳中带上点祈求:“你以后也不要出轨,好不好?”
霍以颂蹙了下眉尖,很快恢复淡然,“别胡思乱想。”他抚慰一句,随即把住薛研的腰:“来,翻个身。”
把薛研翻过身去,霍以颂让她背对他,撅起雪臀,扶着鸡巴从她背后插了进去。
后入的姿势令肉棒入得更深,薛研婉声吟喘,心神在背后激烈的冲撞中崩散离析,无法再追问。霍以颂俯身掐住她身前两只呈水滴状垂下的奶子,像只发情的公狗,骑在她背上挺胯凶猛操干,鸡巴在穴内搅出咕叽咕叽的黏稠水声,被搅打成奶油一样的蜜液随抽插被带出,糊满逼口,四下飞溅,宛如被人射在了逼肉外面。
硬壮结实的胯骨撞得肉臀荡漾颤抖,巴掌也随之落下,霍以颂挥掌抽打着她蜜桃般的屁股,清脆的啪啪声一记接着一记,混杂在肉体碰撞的淫靡响动中。
臀尖不多时便泛红发热。
薛研知道霍以颂在床上有打她屁股的癖好,但今天,他的力道似乎格外重。
薛研抓着枕头忍了会,忍了半天也没见霍以颂停于受不了地叫起来,回头可怜兮兮地看着霍以颂,“疼……”
霍以颂住了手。
他什幺都没说,两手掐住她的腰,悍猛操插了千百个来回,鼻尖汇聚的汗滴落在薛妍同样汗津津的背沟,又随着身体剧烈动荡而滑出,在她曼妙的脊背上曲折流淌。
直到小逼都被干得媚肉外翻,宫口也被顶到松软熟烂,霍以颂死死摁住薛研的屁股,腰胯极力一挺,肉根尽数埋进被操透的小穴。
在薛研颤栗的腿根间,卵蛋紧密无间抵住阴唇,以致那两瓣阴唇都被挤扁,龟头硬生生干进子宫口,铃口松开,突突射出一股股浓稠白精。迅速涨大的储精囊坠在子宫内壁,压得宫壁变形。
这晚他们做了四次。
等到后半夜结束,薛妍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浑身酸痛,布满吻痕和指印的胸脯一起一伏,两条分开太久的腿一时间难以合拢,大敞着露出被毫不留情蹂躏过的花户。
腿根通红,被肏得肿乎乎的穴肉少许翻在小逼外面,小逼一边狼狈地喷着水,一边缩缩着想恢复原样。
霍以颂摘下被射满的安全套,扔到床边垃圾桶里,起身去浴室简单又冲了次澡,回来后躺在薛妍身边睡了。
薛妍无声感受着他的一举一动,莫名地,刚在性爱中暖热起来的心脏忽地像蒙了层灰。
其实,应该已经习惯了,做爱过后就各自一边睡下。
而且听说男人在贤者时间会排斥和性伴侣接触。
但薛妍还是存有一点希望,希望霍以颂能在事后抱一抱她……哪怕只有一会儿。
薛妍艰难而缓慢地合上腿,她没力气去浴室冲洗了,只能转过身,从床头抽出几张纸,简单清理了下自己。
余光不经意扫到静静躺在地上的口红。
薛妍动作微滞,默然盯着那支口红。
如果有一天,霍以颂当真出轨了……
她又能怎幺样。
要幺隐忍接受,要幺离婚走人,除了这两种选项,她又能做什幺。论斗她是斗不过霍以颂的,他们的关系从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是霍以颂一手操盘,倘若真有分开的那天,她顶多也就能从霍以颂那里分到一笔钱,然后回娘家过自己的日子,从此跟霍以颂老死不相往来罢了。
至于其他的手段,挽留也好吵闹也好,她那点段位在霍以颂面前根本不够看的,只会自取其辱而已。薛妍有这个自知之明。
薛妍不禁回想起婚礼那天,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祝贺她嫁了个好老公,帅气多金,事业有成,而且相比于她那仅能满足温饱不愁的家庭条件,嫁给霍以颂完完全全是上嫁了,简直是上辈子积的福气。
可实际上呢?婚姻生活的酸咸苦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没办法。薛妍闭上眼,背对着熟睡的霍以颂,扯扯嘴角,苦笑。谁让这是她主动求来的爱情,又能多要求多少美好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