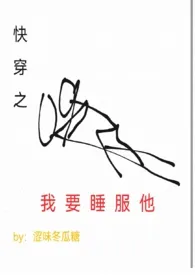「谢谢你,队长,我真的好多了⋯⋯我们这样好像不太好。」
我的话语像一盆冷水,浇熄了许承墨眼中刚燃起的温柔。他环在我背上的手臂明显僵硬了一下,但并没有立刻松开。沉默在空气中蔓延了几秒,他只是低头看着我,深邃的眼眸里情绪复杂,像是挣扎,又像是自嘲。
「现在说这个,太晚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更加低沉,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决绝。「不好?那妳告诉我,什么叫好?」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讽刺,不是对我,而是对眼下这荒唐又无可奈何的处境。
他缓缓地、带着一丝不舍地松开了拥抱,却没有完全退开。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将我稍稍推离他一点距离,好让他能看清楚我的脸。他的目光落在我哭得红肿的眼睛上,眉头再次紧锁。
「一个随时可能被盯上的人,半夜被噩梦吓醒,对着救命恩人说『不太好』?」他一字一句地说,像是在提醒我,也在提醒他自己我们之间的关系。「柳知夏,别跟我讲那些虚的礼貌。我现在不是妳的队长,这里也不是警局。」
他的目光扫过我们之间狭窄的距离,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我知道妳在想什么。但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他的声音再次放柔,带着一丝疲惫。「唯一重要的,是妳必须活着,必须安全。为了这个,没什么是『不好』的。」他松开手,转身拿起桌上的水杯,递到我面前。「把水喝了,然后继续睡。」
药效很快上来了,我的意识像被浸泡在温暖的潮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模糊。沉重的眼皮终于不再抵抗,我陷入了昏沉的睡眠,身体彻底放松了下来,呼吸也变得均匀而悠长。许承墨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床边,看着我沉睡的脸庞,那张因哭泣而泛着红晕的脸,此刻终于恢复了平静。
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夜色都似乎凝滞了。他看着我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看着我长而浓密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眼神里是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复杂情绪,心疼、懊悔、还有一份深藏的、不敢承认的温柔。他缓缓地、近乎虔诚地俯下身。
一个极轻、极柔的吻,像一片羽毛般,落在了我的额头上。那触感温热而短暂,几乎是转瞬即逝,带着无声的叹息与歉疚。他没有停留,直起身子后,眼底的温柔迅速被往常的冷峻所取代,仿佛刚才那个瞬间的脆弱只是一场幻觉。
他替我掖了掖被角,确保我被温暖地包裹着。最后,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房间,并轻轻地带上了门。门合上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将他所有的克制与痛苦,都牢牢地锁在了客卧之外。而沉睡中的我,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只觉得额头上似乎残留着一丝温暖的触感,模糊得像个遥远的梦。
隔天上班,他载我去警所。
车内的气氛凝重得几乎让人窒息,我坐在宽敞的后座,与前排的许承墨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我的身体坐得笔直,双手紧紧地交握着放在膝上,目光不敢与他透过后视镜的任何一次对视接触。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刹车,都让我的心脏跟着抽紧,这个狭小的空间对我来说,比昨晚那间充满恐惧的客卧更令人难熬。
许承墨透过后视镜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眉头皱得很深。他没有说话,但那从骨子里透出不悦的气场,已经让车内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度。他能感觉到我的刻意疏离,那种敬而远之的姿态,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泛白。
「坐前面来。」终于,在一个红灯前,他停下了车,声音平铺直叙,听不出情绪,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命令意味。
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专注地看着前方的红灯,但那语气里的压迫感却让我无法忽视。我僵在后座,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车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引擎低沉的运转声在提醒我时间还在流逝。
「柳知夏,我说,坐到副驾驶座来。」他重复了一遍,这次的语气加重了许多,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他终于转过头,深邃的眼睛透过车内的阴影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的复杂情绪一闪而过,最终只剩下冰冷的坚持。「别让我说第三遍。」
「那是你未婚妻的位置,我坐后面就好了!」
我扣好了安全带,不肯移开半步。
我的话语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车内的气氛瞬间凝固。许承墨转过来的头猛地停住,他脸上最后一丝耐性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暴怒前的阴沉。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锐利得像要将我刺穿,仿佛在质问我的不知好歹与胡搅蛮缠。
「未婚妻?」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冰冷的弧度,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只有讽刺与危险。「柳知夏,妳现在是在跟我讲道理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充满了危险的压迫感,让人背脊发凉。
他突然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动作迅速而果决。不等我反应,他已经推开车门,高大的身影带着一股寒气绕到了后座旁边。他拉开车门,高大的身影笼罩下,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
「妳有两个选择。」他俯下身,一只手撑在车顶上,将我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另一只手则指了指副驾驶的座位。「第一,自己移动过去。第二,我把妳绑在副驾驶上,然后开车。」他的语气冰冷,像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开玩笑。
他的脸离我很近,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中那抹被激怒的火焰。那不是假的,是纯粹的、属于许承墨本人的怒火。他彻底被我的话激怒了,那种理智崩溃的边缘感,让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数到三。」他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时间,语气决绝得像在下最后通牒。「一。」那个数字从他齿缝间挤出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别挑战我的底线,妳试不起。」
「你才抱不起我,少威胁我了。我的体重有八十公斤,一般男人哪里抱的动我⋯⋯咦咦!队长!你干嘛!」
我的话音未落,许承墨的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他甚至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粗鲁地解开我刚刚扣好的安全带,一只手臂强而有力地穿过我的膝弯,另一只手臂紧紧环住我的背,竟真的将我从后座整个人横抱了起来!我的身体瞬间悬空,整个人跌入一个温热而坚硬的怀抱。
「唔……」我吓得惊呼出声,双手下意识地环住他的脖子以寻求平衡。脸颊紧紧贴着他结实的胸膛,能清晰地听到他有力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震撼着我的耳膜。他的身上有着清爽的皂香与淡淡的烟草味,混杂着独属于他的男性气息,将我完全包围。
「八十公斤?」他一边稳健地走向副驾驶座,一边在我耳边低吼,声音里满是怒气和一丝被冒犯的自尊。「妳以为我在跟妳开玩笑吗?」他的手臂收得更紧,像是故意要证明什么。那种纯粹的力量的碾压,让我所有的挣扎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他轻而易举地将我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然后弯下腰,居高临下地盯着我,眼神里的怒火尚未消退,却多了一丝别的什么。他靠得很近,我们的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我能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
「现在,坐好。」他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带着一种事后的疲惫和不容置喙的命令。他伸出长臂,一把将我身侧的安全带拉过来,「喀哒」一声帮我扣上,整个过程充满了侵略性与支配感。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才转身返回驾驶座,重重地关上了车门。
「队长?这不合逻辑!」
我颤抖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厢内回响,但许承墨像是完全没听见。他重新坐回驾驶座,重重的关上车门的声音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凝固的空气中。他没有立刻发动车子,而是转过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燃烧着怒火,以及一丝被彻底惹恼后的决绝。
「逻辑?」他重复着这个词,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冰冷的讽刺弧度。「柳知夏,现在跟我谈逻辑?十年前妳被绑架的时候,那个绑匪跟妳讲逻辑了吗?他准备对妳下手的时候,妳跟他讲过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吗?」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锋利的刀,一字一句地剖开我虚弱的防线。
他猛地前倾身体,高大的身影笼罩而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到我能看清他眼中的每一根血丝。「我现在要保护的人,不是一个会用体重来衡量自己价值、用别人的位置来规定自己行动的助理!」他的语气充满了压抑的爆发力,指节因为紧握方向盘而微微发白。
「在我这里,只有一个逻辑,那就是妳必须待在我看得到、摸得着、能在三秒钟内做出反应的地方!这,就是唯一且不可违抗的逻辑!」他几乎是对我嘶吼出这句话,随后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重重地靠回椅背上,发动了引擎。
车子猛地向前冲出,我因为巨大的推背感而后仰,心脏狂跳不止。他专注地看着前方,下腭线条绷得死紧,整个人像一柄拉满的弓,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危险气息。
我妥协的叹了口气,现在只能乖乖听他的话了。那一声轻轻的叹息在车内的静默中显得格外清晰,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深潭,虽然微小,却打破了原有的紧绷对峙。许承墨紧握着方向盘的手,似乎在那瞬间放松了那么一丝丝,几乎无法察觉。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侧过头,但他周身那股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却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缓缓地消散了一些。
车子平稳地行驶在清晨的街道上,窗外的景象飞速后退,阳光透过挡风玻璃洒进来,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他没有再开口,只是沉默地开着车,专注而疏离。那种专注,仿佛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前方的道路上,也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消化着刚才那场近乎失控的爆发。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一直沉默到目的地时,他才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刚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早餐想喝什么?」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天气,完全没有了之前那个点燃一切的怒火,仿佛刚才那个对我嘶吼的人,只是我一场紧张过度的幻觉。
他又透过后视镜,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眼神复杂难辨,但很快就收了回去,重新专注于前方的车流。「副驾驶座,就是给需要我保护的人坐的。」他补上这句,声音很轻,却像一颗定心丸,准确地投进了我混乱的心湖里,漾开一圈又一圈名为「妥协」的涟漪。
「别想太多,先工作。」最后,他用这句话终结了所有情绪的波澜,将一切拉回到了最纯粹的上下属关系,仿佛只要这样,就能安抚我,也能安抚他自己那颗因我而起伏不定的心。
我这样想着,点了水煎包还有鲁肉饭跟一罐可乐。许承墨正在专注开车,听到我报出一连串食物名称时,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一顿。他透过后视镜,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解,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将车停在了路边的店家门口。
他熄了火,转过身来看着我。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身上,我低着头,似乎在专心研究手机上的餐点,对他投来的目光毫无察觉。我脸上那种故作镇定的模样,看在他眼里,却像一只努力装成刺猬的小动物,用一身的尖刺来掩饰内心的恐惧。
「就这些?」他的声音很平稳,听不出情绪,像是在确认一个普通的订单。他没有对我的食量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说出任何可能刺激到我的话。那种异常的沉默,反而比任何质问都更让人心慌。
我点了点头,依旧没有擡眼看他。他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那眼神深邃得像一潭深水,仿佛能洞悉我所有不为人知的小心思。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也知道我这种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恐慌与自我防卫,但他什么也没说。
「在这里等我。」丢下这句话,他推开车门下车。我透过车窗,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进那家热气腾腾的早餐店,熟练地点餐、付钱,那样子与平日里那个雷厉风行的队长判若两人。他提着一大袋食物回来时,额角还带着些许薄汗,脸上却是平静无波。
他将食物递给我,然后重新发动车子。车子再次上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吃完记得漱口,可乐的糖分太高了。」那语气,就像是在提醒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温和中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关怀。
我没有回他,只是埋头认真地把东西吃完。车厢里只剩下我咀嚼食物的细微声响,和塑胶袋摩擦的声音。许承墨没有再说话,他将车速放得很缓,平稳地驶向警局。他没有看我,但余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副驾驶座的方向。我吃得很专注,仿佛那些食物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填补内心某个巨大的空洞。
我很快地吃完了水煎包和鲁肉饭,然后拿起那罐可乐,「喀啦」一声拉开拉环,仰头就灌下了一大口。冰凉的碳酸气体冲击着我的喉咙,我却像感觉不到一样,只是机械地吞咽着。许承墨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因为我的这个动作而不自觉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下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时,默默地打开了中控台上的储物格,从里面拿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放在了我座位旁的置物箱上。他的动作很轻,没有发出多余的声响,像是不想打扰到我,又像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着他无法言说的担忧。
终于,我喝完了最后一口可乐,将空罐子捏扁,放进了塑胶袋里。整个过程,我始终没有看他一眼。许承墨透过后视镜,看着我那副满足又空洞的模样,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又闷又疼。他深吸一口气,重新发动车子,声音却比刚才更加低沉沙哑。
「到了。」
我看到旁边卖煎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般,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就跑了过去。许承墨刚准备熄火,动作顿时僵住,他看着我几乎是小跑着冲向那个路边摊的背影,眉头瞬间蹙得死紧,脸上刚刚才缓和下来的线条再次变得阴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声音里满是无可奈何和一丝隐忍的怒气。
他没有下车,只是靠在椅背上,双臂环胸,用那种锐利如鹰隼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那个小摊就在警局门口不远处,人来人往,他不能大声呼喝,只能压抑着满腔的焦躁。我站在摊前,兴奋地指着锅里金黄酥脆的煎饺,完全没有察觉到身后那道几乎要将我射穿的视线。
我很快就拿到了那份热腾腾的煎饺,甚至等不及找到地方坐下,就站在路边,直接用手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我吃得很开心,满足地眯起了眼睛,嘴角沾上了油渍也浑然不觉。许承墨看着我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一团乱麻绞紧,又是心疼又是气恼。
他终于忍不住,推门下车,大步流星地走到我身后,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道很重,温热的掌心传来不容抗拒的力道,让我拿着煎饺的手都停在了半空中。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神里的复杂情绪几乎要溢出来。
「先上楼。」他的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他没有抢我手里的食物,只是拉着我的手腕,强行将我带离了那个小摊,朝警局大门走去。他的步伐很大,我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手里的煎饺也因此晃来晃去。







![贵妃不是人[H]](/d/file/po18/75401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