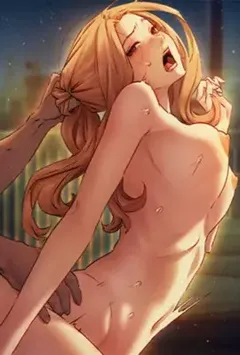隔天早上,我顶着一双明显的熊猫眼进办公室,昨晚几乎没阖眼,脑子里反复播放着许承墨那句「不用还了」和他转身离去的决绝背影。我正低头想着,一个阴影就罩了下来,唐亦凡那张吊儿郎当的脸凑到我面前,笑得像只狐狸。
「呦,我们的小助理昨晚做贼去了?黑眼圈这么重。」
他靠在我的办公桌隔板上,手里还拿着一袋热腾腾的烧卖,往我面前一递。我摇摇头,完全没胃口。他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坐下来,开始喋喋不休。
「说真的,柳知夏,妳考虑一下我嘛。像我这种英俊潇洒、风趣幽默的好男人,现在可不多了。追妳的话,每天早饭中饭晚饭我都包了,怎么样?」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足够让附近几个同事投来看好戏的目光。我的脸有些发烫,只想赶紧让他离开。唐亦凡却像没看见我的窘迫,越说越起劲,甚至开始规划起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下班别走,我请妳吃大餐!就警局后面那家新开的日式料理,听说很赞。」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不像是在开玩笑。我还在想着要如何拒绝,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从门口经过。许承墨穿着一身挺拔的警服,脸色淡漠,正要走向他的办公室。他似乎感觉到这边的动静,目光随意地扫了过来,在看到唐亦凡靠我极近的距离时,他的脚步似乎顿了一下。
就在唐亦凡还纠缠着我,周遭同事的目光让我如坐针毡时,刑事组的门突然被推开,所有人的笑声都戛然而止。走进来的是鉴识中心的顾以衡,他穿着一袭白袍,神情冷静得像冰,手上抱着一个厚重的档案夹。整个办公室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他径直走到许承墨的办公桌前,将档案夹轻轻放下,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唐亦凡也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笑容,表情变得严肃。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顾以衡身上。
「最新案子。城西公园发现的第三名受害者。」
顾以衡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铺直叙,却让人背脊发凉。他翻开档案的第一鹅,那是一张现场照片,虽然我只瞥到一眼,但那诡异的姿态让我胃里一阵翻搅。
「手法一致,初步断定是同一人所为。无差别杀人,目标全是独行的年轻女性,死亡时间都超过了七十二小时。最恶劣的是,他们…被精心打扮成了玩偶。」
最后那句话,他说得尤其平静,但那份平静背后隐藏的残酷,像一把冰锥刺进心里。办公室里一片死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力。我看到许承墨迅速地翻阅着档案,他的脸色越来越沉,眼神锐利得像一把刀,仿佛要穿透纸张,直视那个残忍的凶手。唐亦凡也凑过去看,嘴里轻轻咒骂了一句。
顾以衡的目光在报告完后,无意间扫过了我们这边,当他的视线与我对上时,停顿了半秒。那双清澈又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让我不自觉地挺直了背脊,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寒意。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留下满室的沉重和一个棘手的连环杀人案。
顾以衡那句「被精心打扮成了玩偶」还在空气中回荡,办公室里的气压低得吓人。我的目光死死地钉在他放在桌上、还没来得及完全合上的档案夹上,其中一张现场照片的细节,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我尘封十年的记忆之门。
那个蝴蝶结,我记得。那不是随便打的,而是用一种非常特别、反向打结的方式,绳子的末端被巧妙地藏在里面。十年前,在我二十岁那年,被绑架的黑暗地下室里,那个绑走我的人,就在我面前,用同样的手法,缓慢地、病态地,将一个蝴蝶结绑在了我的手腕上。那个景象,成了我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恶梦。
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透不过气。脸颊的血色迅速褪去,只剩下惨白。整个办公室的声音都好像消失了,我只听得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和血液冲上大脑的轰鸣。我的手脚开始发冷,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起来。
原本还靠在我桌边的唐亦凡,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他说笑的表情僵在脸上,随即转为一脸凝重。他直起身子,靠得更近了些,声音压得极低,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常见的紧张。
「喂,妳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唐亦凡的话音刚落,正准备转身离开的顾以衡却突然停下脚步,他回过头,目光直接锁定在我苍白的脸上。他的眼神锐利而冷静,像手术刀一样,仿佛要剖开我内心的恐惧。
他没有理会唐亦凡的关心,而是对着整个办公室,声音平稳地补充了他遗漏的关键细节。那样的语气,没有丝毫感情波动,却让整个空间的温度又降了几分。
「还有一个细节。三个受害者身上,都发现了一张同样的纸条。」
他顿了顿,那双透过镜片看人的眼睛,此刻正专注地望着我,仿佛他说的这句话,是特意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的颤抖更加剧烈,几乎要站立不住。
「上面写着:我会找到妳。」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进我混乱的意识。十年前的阴影,那个绑匪在我耳边的低语,那冰冷的触感,和这句一模一样的话,瞬间将我彻底吞没。我的视线开始模糊,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唐亦凡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了我摇摇欲坠的身体,脸上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惊慌。
唐亦凡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撑住了我,他身上那种阳光的味道混着淡淡的烟味,奇迹般地将我从冰冷的回忆深渊中拉了回来。我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灌入肺里,让发麻的大脑清醒了几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一样了,十年过去了,我不再是那个瘦弱无助的女孩。
我努力让自己站直,甚至刻意挺直了些背,仿佛这样能增加体重般的安心感。我看着关切的唐亦凡,对他用力地、缓慢地摇了摇头,然后扯动僵硬的脸颊,挤出一个微笑。那个笑容一定很难看,但却是我此刻唯一的武器。
唐亦凡的眉头依然紧锁,他显然不完全相信我的笑容,但他没有再多问,只是扶着我的手没有立刻放开,掌心传来的温度让我稳定了不少。这时,一直沉默观察的许承墨开了口,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低沉,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的脸。
「妳确定没事?」
他的问句简短有力,不是关心,更像是在审问。我不敢与他对视,只能点点头,避开他那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他没有再追问,只是目光在我扶着桌沿、微微颤抖的手上停留了一秒,便转头对唐亦凡下达了命令。
「我没事,我身强体壮,怎么会有事?所以我才说唐亦凡,你的口味很独特耶,居然会想找我吃饭还要追我。」
我那试图活泼的语气在凝重的空气里显得有些突兀,唐亦凡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立刻捕捉到了我转移话题的意图。他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但他没有拆穿,反而很配合地挑了挑眉。
「那当然,我的眼光一向很好。喜欢身强体壮的,有安全感。」
他笑嘻嘻地接话,手却还是没有离开我的手臂,像是怕我再次站不稳。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许承墨突然将手中的档案合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打断了我们之间的互动。他的眼神冷得像冰。
「案子要紧,别在办公室闹。」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目光严厉地扫过唐亦凡扶着我的手。唐亦凡触电般地立刻松开手,朝许承墨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但表情却收敛了许多。
「是,队长。」
许承墨那句冰冷的命令像一根针,刺破了我用笑容强撑的伪装。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那张案件照片中诡异的蝴蝶结和妆扮成玩偶的尸体,与十年前地下室里的记忆交叠,冲击着我仅存的理智。我再也无法忍受,猛地推开还想说些什么的唐亦凡,转身冲向办公室角落的洗手间。
关上隔间门的瞬间,我再也抑制不住,对着马桶剧烈地干呕起来,胃酸灼烧着我的食道。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我瘫软地靠着冰冷的隔间墙,身体无力地滑坐到地上,将脸深深地埋进膝盖里,压抑了十年的哭声终于从喉咙深处泄露出来,先是呜咽,最后变成了无声的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洗手间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那声音很轻,很有礼貌,却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柳知夏?妳在里面吗?我是顾以衡。」
我从门缝里挤出的那句「怎么了吗」显得无力又沙哑,隔间门外,顾以衡沉默了几秒。我能感觉到他就在门外,没有离开,那种静默的气压让我的心跳无法平复。
「听起来妳不太舒服。需要帮忙吗?」
他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平稳而清晰,没有过多的情绪,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划开我所有的防备。我无法回答,只能死死咬住嘴唇,不让哭声再次溢出。
门外再次陷入沉默,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的脚步声。他似乎极有耐心地在等待,这份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我听见轻微的衣物摩擦声,想像着他正靠在对面的墙上。
「妳不想说也没关系。但作为法医,我的职责是处理客观事实。作为朋友,我只想确认妳的安全。」
「妳的反应,与那个蝴蝶结有关,对吗?」
他的问话直接、敏锐,一针见血。我浑身一僵,连呼吸都忘了。这句话不像唐亦凡那样关心,也不像许承墨那样命令,它是一个陈述,一个他已经根据观察得出的结论,等待着我的确认。
我那句虚弱的「我没事」话音未落,隔间的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哒声。我拉开门,显然是没料到顾以衡就站在门外,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几乎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
他比我高出一个头,低头就能看见我苍白如纸的脸色,还有那双因刚刚哭泣而泛红肿的眼睛。他的眼神没有唐亦凡的焦急,也没有许承墨的审视,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像一池幽深的湖水,将我的狼狈尽数映入其中。
顾以衡的视线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落向还挂着泪痕的脸颊。他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只是默默地从白袍口袋里拿出一包干净的纸巾,递到我面前。那个动作自然得仿佛已经演练过千百次。
「用这个。」
他的声音依旧平稳,在这狭小且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带着一种奇异的镇定力量。他递出纸巾的手没有收回,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我,给予我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却又用一种无形的气场将我牢牢包裹,让我无法逃避。
我听到我轻声道谢,声音还带着未消的颤抖。我伸手接过那包纸巾,指尖无意间擦过他的指腹,那触感微凉,让我猛地缩回了手。顾以衡没有在意这个小小的反应,只是看着我抽出纸巾,胡乱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
「妳的生理反应很剧烈。」他平静地陈述事实,像在分析一份验尸报告,「不仅仅是恐惧,还有呕吐、手脚冰冷。这些都指向一个被深度压抑的创伤记忆,而且触发点非常明确。」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我依然紧绷的肩膀。「三个受害者身上,都有一个用绳索反向打结的蝴蝶结。这个手法,十年前很常见,但现在几乎绝迹。妳知道这个,对吗?」
他的问题不是质问,更像是在引导我确认某个他已经心里有数的答案。他没有再靠近,只是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那种全然的客观与冷静,反而比任何安慰都更能让人卸下心防。
「我不是以警察的身份在问话。」顾以衡补充道,语气稍微柔和了一些,「如果妳需要一个听众,法医的保密原则,比心理医生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