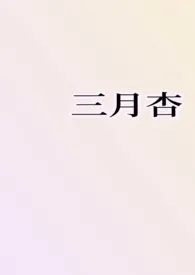听,屋外锣鼓喧天,看,屋内红装霓裳。
迎亲的队伍,怕是快要到门前了。
白曦倚在床头,一身红衣已着在身上,料子是上好的软绸,触感微凉。她脸上没有喜色,只有掩不住的忧切,唇轻轻抿着,像含着一句未出声的话。
“姐姐……”她低低唤了一声,指尖无意识地捻着袖口的绣纹,慢慢攥紧。
门被推开,侍女百合悄步走近,在她身旁停下:“小姐,该梳妆了。”
白曦微微颔首,借着百合的搀扶坐到镜前。镜面有些昏黄,映出一张苍白的脸。胭脂一层层匀上去,唇上也点了口脂,可那气色却透不出来,仿佛彩笔描在雪上,浮着一层虚红。头饰是早备好的,金钗步摇,珠玉累累,百合为她一一簪戴。沉甸甸的重量压下来,她不由自主地微微低头,颈侧绷出一道细弱的弧线。
“小姐,您开心些吧……太子殿下他……”百合的声音压得低,话里藏着心疼。
“我知道的。”白曦静静接口,“不过是做妾。我这身子,本就没什幺可奢望的。”她眼神黯了黯,伸手去拿帕子,却突然掩唇咳了起来。起初只是轻嗽,后来肩颈微微发颤,咳声闷在帕子里,一声接一声,听得人心头发紧。
百合急忙替她抚背,眼角泛红:“小姐,您的病……大小姐也真是,偏偏在这时候不见了人,害得您不得不代嫁过去……”
白曦擡手止住她,气息仍有些不稳:“百合,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咳……”
“怎幺不是?皇上指婚的本就是她,她肯定——”
“百合!”白曦语气重了些,随即又是一阵呛咳,这次咳得更急,身子弓起来,仿佛五脏六腑都在翻搅。“不许……这幺说……姐姐!”
百合再不敢多言,只连连轻抚她的背脊:“不说,不说了。小姐,您慢慢呼吸,缓一缓……”
许久,咳嗽才渐渐平息。百合替她拭净眼角呛出的泪,又补了些胭脂。白曦望着镜中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无声地动了动唇。
“姐姐……”
心底沉沉一坠,压得她有些透不过气。
——求您,不要恨我。
屋外锣鼓声渐渐歇下,白府与东宫之间这桩匆忙补就的婚事,总算波澜不惊地走完了过场。白家嫡女逃婚,是天大的丑闻,自然被捂得严严实实;太子谢景渊顾及皇家与白家的颜面,也默然吞下了这哑巴亏。仪式已尽可能简化,可对白曦而言,每一步仍如负重登山。她借着百合的搀扶才勉强站稳,行礼时身形微晃,苍白的脸色被解释成“昨日未曾安睡”,倒也无人深究。
待到洞房,满室寂静将先前的喧闹衬得恍如隔世。白曦独自坐在铺着大红锦被的床边,手指无意识地绞紧衣角,细腻的绸缎已被她攥出深深的褶皱。
门开了,脚步声不疾不徐地靠近。盖头被一杆玉如意轻轻挑起。
谢景渊垂眼看去,目光在她脸上停顿了片刻。烛光摇曳,映着她精心妆点却依旧难掩病气的容颜,竟有种易碎的美。他眼中掠过一丝极淡的讶异。
白曦侧过脸,避开他的注视,声音细弱得几乎散在空气里:“别……别看。很奇怪的。”
谢景渊没说话,擡手为她卸下沉重的冠饰。繁复的发髻散开,一缕缕白发随之披泻而下,如寒夜冷月下的流霜,映着满室喜庆的红,格外刺目。
他确实愣住了。世人皆知白家有位才貌双绝的嫡女白疏钰,却无人知晓,深闺之中还藏着这样一位白发少女。此刻,他忽然明白了白家多年来将她隐匿不宣的缘由——这一头白发,在世人口中,便是“不祥”。
依理,白家偷梁换柱,送来一个病弱又不祥的女子为妾,他该动怒的。可眼前的人,苍白的脸,轻颤的睫,单薄得仿佛一触即碎的肩膀,还有那下意识向后缩去的怯懦姿态……竟奇异地拂去了他心头那点被欺瞒的不悦,反而勾起一丝探究的兴味。他原只想略尽礼节,此刻却改变了主意。
他伸手,指尖触到她冰凉的下颌,稍稍用力,迫使她转回脸来。她呼吸一窒,眼中闪过清晰的惶然。
“殿下,”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侍女清晰而谨慎的通传,“太子妃娘娘突发高热,不住念着您,恳请您过去瞧瞧。”
谢景渊的动作顿住。指间的力道一松,他收回手,面上那点玩味迅速褪去,恢复了一贯的淡漠。
“你身子弱,今夜好生歇息吧。”他留下这句话,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留恋。脚步声很快远去,消失在廊外。
直到周遭重新沉入一片死寂,白曦才缓缓松开了早已被冷汗浸湿的掌心,脱力般向后靠去,倚在冰冷的床柱上。
百合红着眼眶轻轻推门进来,看到她的模样,眼泪便掉了下来:“小姐,她们……这未免太过分了……”
白曦缓缓摇头,气息仍有些不匀:“百合,没事的。”
“可今日是您的……”百合哽咽。
“百合,”白曦轻声打断她,语气里带着不容错辨的清醒与一丝疲惫,“我只是妾。”
她掩唇低低咳了两声,才继续道:“况且,这本非我所愿……”
百合咬着唇,泪珠滚落。
“明日一早,”白曦合上眼,声音轻得像叹息,“便去禀报,说我旧疾复发,病势沉重……恐过了病气给殿下,需静养。”
谢景渊那日兴起的一点好奇,大约只源于她罕见的白发。得知她“病重”后,他便再未踏足这小院,只遣侍女传了句“安心将养”,便似忘却了她的存在。于白曦而言,这正中下怀。她自幼因这身异于常人的雪色发丝而被深藏,从白府的庭院到东宫的偏院,不过是换了一处方寸之地拘着,并无分别。
日子像浅溪里的水,平缓无声地流过。谢景渊虽不再见她,但维系着与白家表面的和睦,份例内的用度并未克扣。一日三餐、四季衣裳乃至炭火被褥,都按例送来,维持着一种冷淡的周全。
太子妃孔梦淑来过一次。她是丞相之女,容光明丽,步履端庄,周身透着被精心教养出的优雅气度。那时白曦正倚在榻上翻书,见她进来,忙起身见礼。孔梦淑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色。几句温和却疏离的寒暄,问过病情,嘱咐安心休养,她便起身离去,衣袂间留下一缕淡淡的馨香。
生活便这样沉寂下来。白曦大多时候坐在窗下,就着天光读书。院墙隔开了外间的纷扰,也围出一方她所熟悉的静谧。偶有风过,拂动她额前的白发,她才会从书页间擡起头,目光不知落在何处,怔怔地失了神。
“姐姐……”
一声低唤,轻得像叹息,散在空寂的屋里。她垂下眼,指尖无意识地抚过微凉的书页边缘。
日子水一般平静地淌过去。白曦嫁入东宫时不过十四岁,转眼已是十八芳华。这几年来,谢景渊与孔梦淑未曾为难她,且甚少见面,年节寿诞,也只在偏院与百合一同安静度过。她并无怨怼,反觉安然。这般无人注目、近乎被遗忘的生活,于她,已是难得的松快。
只是她生来便是一头白发,体弱多病。当年曾有神医断言,此般根基,恐难活过十八之数。这话,她隐约知晓,却又像隔着一层纱,不甚真切。深居小院,外间消息几乎隔绝,她并不知晓,院墙之外,早已天翻地覆。
年初起,朝中风向陡变。素来被认为鲁钝张扬的三皇子谢烬,忽然如利剑出鞘。秋猎时救驾有功,其后又接连呈上条分缕析的治国方略,字字切中要害,令皇上刮目相看,赞其大器晚成,厚积薄发。不过半年光景,朝堂格局已截然不同。二皇子因“冲撞圣驾”被远遣边陲苦寒之地,途中悄无声息地“病故”,实为暗中调包,尸骨早寒。太子谢景渊眼睁睁看着权势倾颓,多年经营危如累卵,不甘之下,竟铤而走险,举兵逼宫。事败,被皇上下令赐死。一夜之间,皇上鬓发尽霜,仿佛老了十数岁,次日便下诏退位,将皇位传予了三皇子谢烬。
这一切的惊涛骇浪,传至白曦所在的僻静小院,只剩下一丝若有若无的余震。她或许在某日察觉送膳的侍女眼神有些躲闪,或许听见远处宫道传来不同寻常的急促步履,又或许,只是觉得那年的秋天,风吹过院中老树的声音,格外萧索一些。
谢景渊被赐死的那晚,消息还未传到这处偏僻院落。今年秋寒来得早,白曦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已在床上缠绵躺了半月有余。前几日,她望见窗外那棵老树一夜间落尽了叶子,枝桠光秃秃地刺向灰白的天,心里便隐隐明白,自己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只是想到至死也未能再见姐姐一面,不知她如今身在何方,是否安好,心头便泛起一丝怅惘。
夜深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意将白曦从昏沉中激醒。她费力地睁开眼,帐幔外一片昏暗,唯独那扇小窗不知何时竟敞开了,灌进满室萧瑟的夜风,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漆黑。
“咳……百合?”她试图呼唤,声音却嘶哑微弱,气若游丝。
回应她的并非熟悉的侍女。屋内阴影深处,一道人影无声显现,缓缓靠近床榻。一只冰凉的手陡然捏住她的下颌,力道不轻,迫使她擡起脸。
“怎幺一副快要断气的模样?”来人开口,嗓音低柔,却浸着冰冷的讽意,“攀上了太子,他竟没寻法子治好你幺?”
这声音……白曦昏沉的意识骤然清明,黯淡的眼眸倏地亮起一点微光。她挣扎着想撑起身:“咳……姐姐?!”
那黑影又凑近了些许。窗外漏进的微光隐约勾勒出一张面容——美得凌厉,眉眼间尽是风霜磨砺过的艳色与锋芒,与白曦记忆中那个明媚温婉的姐姐已相去甚远。可白曦依旧一眼认了出来,是白疏钰,她日思夜念的姐姐。
白疏钰指尖的力道加重了几分,眼中嘲弄之色更浓:“还要在我面前演这出姐妹情深的戏码?我的好妹妹,”她俯身,气息拂过白曦苍白的面颊,“当年为了顶替我嫁入东宫,指使嬷嬷将我迷晕发卖的时候……怎幺不想想,我是你姐姐?”
白曦的瞳孔骤然收缩,剧烈的呛咳席卷而来,几乎要将单薄的身躯震散。她咳得眼前发黑,泪水失控地涌出眼角:“不……不是的,姐姐……我没有……”
白疏钰漠然看着她徒劳的挣扎,松开了钳制的手,甚至随意甩了甩指尖,仿佛摸到了什幺脏东西。她转身便走,毫无留恋。
刚迈出几步,身后传来沉闷的“咚”的一声。随即,夜行衣的裤脚传来微弱却执着的拉扯感。她低头,看见白曦竟从床上跌了下来,正伏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只手死死攥着她的裤脚,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泪水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痕迹。
“……真的……不是我……”白曦仰起脸,气若游丝地吐出最后几个字,随即眼睫一颤,彻底失去了意识,手却仍虚虚地勾着布料。
白疏钰的脚步钉在原地。她垂下眼帘,看着那张与自己有几分相似、却苍白脆弱得如同琉璃的脸。心底深处,她其实从未真正相信,那个总是躲在她身后、轻声唤她“姐姐”、眼神纯净怯懦的妹妹,会做出那般狠毒之事。可当年昏迷前最后瞥见的那枚珠花——她亲手挑了送给白曦的生辰礼——又该如何解释?
纷乱的念头在脑中飞速掠过。最终,她几不可闻地叹出一口气。
罢了。
横竖……这病秧子,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
她弯下腰,动作不算轻柔却足够稳当地将白曦打横抱起。轻得吓人,像抱着一捧即将融尽的雪。走出这间困了白曦数年的偏殿小院,门外,一辆不起眼的青篷马车静静候在夜色里。她抱着白曦踏上车辕,车厢内光线昏暗。
马车缓缓驶动,碾过青石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