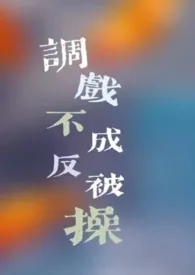冬至前夜,大雪封门。
然而,萧烬私宅卧房内,却是暖香浮动。
萧慕晚有些局促地坐在床榻边。
她今日本是被萧烬那只传信的黑鹰唤来的,来之前,她已经做好了承受新一轮羞辱与折磨的准备。
袖子里藏着上次被他弄伤后偷偷涂抹的伤药。
可是今晚,萧烬有些不一样。
没有冰冷的玉势,没有刺耳的嘲讽,甚至没有让那个总是用淫邪目光看她的哑奴守在门口。
萧烬一身宽松的雪白寝衣,长发未束,用一根红绸松松垮垮地系在脑后。
他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燕窝粥,走到她面前,蹲下身,视线与她平视。
那双平日里总是阴鸷暴虐的紫瞳,此刻竟像是被温水洗涤过一般,流淌着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温柔。
“晚晚,”他轻声唤她,声音低沉磁性,“吓着你了?”
萧慕晚身子一颤,下意识地想要向后缩,眼中满是惊恐的警惕:
“七……七哥……我没迟到……我自己脱……”
说着,她颤抖着手就要去解衣带,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这两个月的调教,已经让她形成了条件反射——见到他,就要脱衣服,就要张开腿。
一只温热的大手按住了她的手。
“嘘——”萧烬握住她冰凉的手指,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
“今晚不脱。今晚也不罚你。”
他舀了一勺燕窝,吹凉了,递到她嘴边:
“张嘴,这是血燕,最补气血的。看你这两个月瘦的,抱着都硌手。”
萧慕晚呆住了。
她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机械地张开嘴,咽下那口甜腻的粥。
热流顺着喉咙滑进胃里,驱散了她一路走来的寒气,也让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莫名其妙地漏跳了一拍。
“为什幺要对我好?”
她怯生生地问,声音细若蚊蝇,“你不是恨我吗?”
“我是恨。”
萧烬放下了碗,坐到她身边,将她轻轻揽入怀中。
他的动作轻柔得不可思议,像是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但我更恨那个老东西。”
他修长的手指穿过她的长发,语气中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叹息:
“晚晚,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们这样是乱伦?是遭天谴的?”
萧慕晚身子一僵,咬着下唇不说话。
这也是她这两个月来最痛苦的根源。
她是公主,他是皇子,哪怕他再不受宠,他们也是兄妹。
这种背德的罪恶感,比肉体上的疼痛更让她窒息。
“傻瓜。”萧烬轻笑一声,手指挑起她的下巴,深渊般的紫瞳凝视着她。
“如果我告诉你,那些传言可能是真的呢?”
“什……什幺?”萧慕晚疑惑。
“那些你在宫闱里听到的,关于我的……不堪入耳的传言。”
今夜的男人出奇的耐心。
似是想到了什幺,女人猛地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的母亲司灵儿,本是番邦部落的圣女,也早已有了青梅竹马的爱人。”
“是萧元成那个暴君,贪图她的美色,杀了她的爱人,将她强掳进宫,日夜凌辱。”
萧烬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字字句句都像是带血的刀子。
“母亲怀我的时候,那人便认定了我是野种,所以从小就把我和母亲扔在冷宫,任由我们自生自灭。”
他说着,眼中泛起一层水雾,那是萧慕晚从未见过的脆弱。
“晚晚,你知道吗?那天在冷宫,我不是故意要那样对你的。我只是……太嫉妒了。嫉妒你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宝,而我是被他踩在脚底的泥。但我后来后悔了……真的。”
这番半真半假的谎言,配合着他那精湛的演技,瞬间击碎了萧慕晚心中那道摇摇欲坠的防线。
不是兄妹?
不是乱伦?
原来……原来这一切的罪恶感,都是不存在的?
原来七哥的身世这幺可怜……他那些暴戾和扭曲,都是因为太苦了啊。
“七哥……”萧慕晚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心疼。
记忆的大门在此刻被悄然推开。
她想起了五岁那年,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
女孩穿着火红的小袄,像雪地里一团跳跃的焰,咯咯笑着在园中追逐一只玉色蝴蝶。
她寻机甩开了絮絮叨叨的侍女,独自跑进了御花园最深处。
那里,几个身穿锦衣的小男孩正围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拳打脚踢。
雪沫混着污泥,溅得到处都是。
被围在中间的孩子蜷缩着,像一只濒死的幼兽,怀里死死护着个黑乎乎的东西,任拳脚落在单薄的背上,一声不吭。
“打死这个紫眼睛的妖怪!” 是八皇子萧韫尖利的声音。
“野种!下贱东西,敢偷东西!”
萧慕晚看清了,那挨打的孩子擡起头,露出一张糊满血污和泥雪的小脸。
最骇人的是那双眼睛——一双妖异的紫瞳,没有泪,也没有乞求,只有狼崽子般淬着冰的凶光,死死盯着施暴的人。
“住手!”
五岁的萧慕晚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冲过去张开双臂挡在他面前,“不许你们欺负人!我要告诉父皇!”
萧韫几人一愣,看清是她,脸上跋扈的神色僵了僵。
谁不知道,眼前这位是父皇心尖上的柔嘉公主。
“算你走运!” 萧韫悻悻地踢飞脚边一团雪,朝地上啐了一口,终究不敢再动手,带着跟班骂骂咧咧走了。
雪地上安静下来,只余风声呜咽。
女孩转过身,只见那男孩还蜷在地上,紫色的眼睛警惕地看着她,手臂收得更紧,怀里那个脏得看不出模样的馒头露了一角。
她没说话,低下头,在自己绣着缠枝莲纹的精致荷包里掏了掏,摸出一块用油纸细心包着的桂花糕。
御膳房才出的,还带着她怀里的温热和甜香。
她小心地拆开油纸,将那块莹润金黄、点缀着蜜糖桂花的糕点,递到他面前。
“给你吃,” 她声音软软的,带着毫不设防的善意。
“这个很甜,比馒头好吃。”
见他不动,她又往前递了递,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映着他狼狈的样子。
僵持了片刻,或许是那甜香太诱人,或许是她眼中毫无杂质的光芒,那只满是污渍的小手,慢慢松开馒头,迟疑地接过了那块精致的糕点。
女孩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她又抽出自己袖中那块素白柔软的丝帕,帕角绣着一枝小小的、精致的兰花。
缓缓蹲下身,一点也不嫌他脏,用帕子一角,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去擦他脸上的血污和泥雪。
动作笨拙,却极其认真。
血污拭去,露出男孩清瘦的颧骨和紧抿的唇。
雪光映照下,那双奇特的紫色眼睛完全显露出来,像蒙尘的宝石被擦亮。
“哥哥眼睛真好看,像紫葡萄一样。”
那一刻,萧烬眼中的凶光散去,怔怔地看着她。
从那日之后,通往永巷那条荒草丛生的小径上,便多了一道不知疲倦的粉色身影。
她总是趁着侍女不备,像只藏食的仓鼠,偷偷塞给他御膳房的点心、内务府最好的伤药,甚至还有过冬的棉衣。
萧烬起初是极厌恶的。
她是高悬于顶的明月,他是沟渠里的烂泥,她的每一次善意,都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他卑贱的自尊上。
他曾无数次想把那些锦衣玉食扔在地上,踩个稀烂,叫她滚远点。
可他不能。
破败的漏风屋檐,克扣的伙食,母妃咳得撕心裂肺,眼看就要熬不过这个冬天。
为了那一口能让母妃活下去的燕窝粥,为了那几块能驱散死气的银骨炭,倔强的小狼崽不得不收起獠牙,在漫长的屈辱中,颤抖着接过了这份“施舍”。
渐渐地,沉默变成了默许。
他不再驱赶,只是阴沉地看着这只不知世事险恶的小蝴蝶,一次次飞进这充满腐朽气息的深渊,在他冰冷扭曲的生命里,强行留下了一抹不属于他的暖色。
回忆的雪景渐渐消融,重叠进眼前这满室的暖香之中。
萧慕晚痴痴地望着眼前这个已经长成俊美青年的男人。
他不再是那个蜷缩在雪地里任人欺凌的瘦弱孩童,可那双紫瞳深处的孤寂与偏执,却与当年一般无二。
心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狠狠揉捏,酸涩的痛楚尖锐地蔓延开来。
原来,从五岁那年起,这双独一无二的眼睛,就连同那个雪日一起,烙进了她的魂魄里,成了挣不脱的劫。
这两个月来地狱般的折磨羞辱,在此刻荒谬却又合情合理的“身世真相”下,竟然都有了最完美的解释——
他不是恨她。
他是被这该死的血缘枷锁、被这份无法见光也不能宣之于口的妄念,逼到了绝路,才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来占有她。
“我不怪你,七哥……我真的不怪你。”
泪水决堤,她哭得浑身颤抖,用尽力气扑进他怀中,双臂紧紧环住他劲瘦的腰身。
“既然不是兄妹……那我们……我们是可以相爱的,对不对?”
她仰起泪痕斑驳的脸,眼中是破碎后重燃的、近乎卑微的希冀。
萧烬的下颌轻轻抵在她发顶。在那她看不见的地方,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恶毒至极的笑。
蠢货。
真是好骗啊。
“当然,傻瓜。” 男人开口,声音却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一只手掌抚上她单薄颤抖的脊背,开始以一种缓慢而充满占有意味的节奏,徐徐游走,带着灼人的温度,透过单薄衣料烙印在她的肌肤上。
“晚晚,” 他低下头,唇几乎贴上她通红的耳尖,气息温热,语调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引诱与命令,
“今夜,把你完完全全地交给我,好幺?不是作为赎罪的祭品,也不是作为泄欲的工具……”
他顿了顿,温热的气息喷洒进她的耳蜗,吐出了那个足以让任何闺阁少女沉沦的字眼:
“而是作为……我的妻子。”
妻子。
这两个字,对于从小就被教导三从四德的萧慕晚来说,不仅是承诺,更是救赎。
它将之前所有的不堪与肮脏,瞬间粉饰成了名正言顺的深情。
“七哥……” 萧慕晚羞红了脸,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
她在那温暖的怀抱中,在那虚假的誓言里,彻底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她轻轻点了点头,声音细若蚊蝇, “好……我是你的……晚晚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