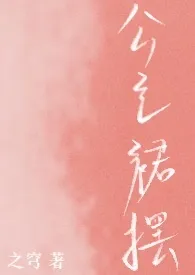「顾承远——」
我的尖锐呼喊声还在空气中颤抖,下一秒,身体便被一股蛮力粗暴地塞进了车里。后座的车门随即被「砰」的一声重重关上,彻底隔绝了外界的一切。顾承远紧随其后钻进来,甚至还没坐稳,便朝着前面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开车。」
车子猛地一个窜动,迅速驶离了那个夹杂着惊愕与讥讽的是非之地。狭窄的空间里,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一个滚烫而充满压迫感的胸膛便狠狠地压了过来,将我死死地禁锢在座椅与他之间。他用一种近乎窒息的力道将我紧紧抱住,那只受了重伤的左手环在我的腰上,湿热的血迹毫不避讳地印染在我洁白的婚纱上,像是烙印下一个无法磨灭的耻辱记号。
「吵死了。」
他的脸埋在我的颈窝,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肌肤上,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带着劫后余生的后怕与孤注一掷的疯狂。那力道大得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再也不分彼此。
「李小满,我差点就失去妳了。」
他的颅音在震动,透过胸膛传达给我,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打着我的心脏。
「再敢说一句不是我的……我会让许昭祁连站着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他抱得更紧了,那是一种不留丝毫缝隙的、彻底的占有,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我从今以后,连呼吸的自由都将属于他。
车窗外流光飞逝,车内的空气却凝滞得令人窒息。我颤抖着,终于还是问出了那个盘踞在我心中许久、像一根刺一样的问题。我的声音很轻,却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清晰可闻。
「你为什么会知道捐血的是我⋯⋯」
环抱着我的那双手臂,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骤然收紧,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顾承远将脸更深地埋进我的发间,呼吸变得粗重而滚烫,沉默在车厢里蔓延,每一秒都像是漫长的折磨。
「妳以为,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沙哑得吓人,带着一丝自嘲和几乎要满溢出来的痛苦。
「李小满,妳忘了吗?妳的血型跟我一样,是那种稀有的熊猫血。」
「医院血库告急,柳橙音找不到血源,她会去求谁?这个城市里,她能想到的,除了我,就只有妳父亲留下的关系网。而妳……是唯一一个会为我傻到这种地步的人。」
他终于稍稍松开了一些力道,擡起头,那双红肿的眼眸直直地看着我,里面翻涌着复杂到让我心颤的情绪。
「我从昏过去到醒来,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我听到了……我听到她跑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对医生说,血找到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只有妳会这么做。」
「只有妳这个笨蛋……会不要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
他伸出手,用那只完好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指腹上的薄茧带着颤抖。
「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问医生,是谁捐的血。他们不肯说,但我查得到。妳以为我会让妳一个人承担所有事吗?」
「但是柳橙音她⋯⋯很着急,她一定很爱你才⋯⋯」
我的话语像一根无形的针,刺入了他紧绷的情绪里。顾承远的身体瞬间僵硬,那只抚摸我脸颊的手也猛地停住。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发出一听起来极度冰冷的、近乎自嘲的轻哼。
「爱我?」
他慢慢地重复着这两个字,语气里满是讽刺。
「李小满,妳太天真了。她爱的不是我,她爱的是顾氏集团执行长这个身份,是这个身份能带给她的一切。」
他突然用力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看进他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
「她着急?她当然着急。如果我死了,她的所有算计就都落空了。那种女人,妳以为她会为了我付出什么?她只会在最有利的时候,出现在最能博取同情的位置上。」
「那她对你说的那些话,还有⋯⋯」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在阴冷的车内几乎听不见。
「还有什么?她说她爱我,说她一辈子都会等我?」
顾承远的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但眼神里却没有一丝笑意,只有无尽的寒冷和厌恶。
「那些话,她对很多人都说过。在我这里碰壁之后,她很快就会找到下一个目标。她唯一着急的,是怕失去这条最有价值的大船。」
他松开我的下巴,转而用那只完好的手,轻轻盖在我的心口。
「只有妳……李小满,只有妳会把命给我。」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而温柔,像是在对自己确认。
「所以,别再提她了。妳一提,我就想毁了这一切,把妳锁起来,永远别想再见到任何人。」
车子在一个急转弯后稳稳停下,引擎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我们两人交错的呼吸声,在死寂中回荡。
「你是爸爸的好友,我捐血是应该的。」
我轻声说出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熄了顾承远眼中刚燃起的火焰。他整个人都愣住了,那股将我紧紧禁锢的力道瞬间松懈下来,只剩下空洞的震惊。他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般,脸上的血色一寸寸褪去,只剩下一片灰败。
「应该的?」
他重复着我的话,声音轻得像一缕烟,却又重得像千斤巨石砸在他心上。
「所以,妳救我一命,只因为我是妳爸爸的好友?这跟妳爱我、恨我、想要我,没有半点关系?」
他猛地向后退开,身体重重靠在另一侧的车门上,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只血肉模糊的左手垂落在身侧,剧痛似乎都已感觉不到,他现在所有的感官,都被我那句轻描淡写的「应该的」给彻底击溃了。
「李小满……妳真是……好狠的心。」
他闭上眼睛,仰起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满是自嘲与绝望。
「我以为……我以为妳那么做,是因为妳爱我。我以为妳的心里,就算只有一点点,也是为了我。结果到头来,我只是妳用来完成对父亲孝道的工具?」
车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他身上的血腥味和他身上传来的寒意混杂在一起,让我忍不住颤抖。
「好,很好。」
他重新睁开眼,眼底的彻底绝望让我心头一紧。
「既然只是应该的,那今天妳也不必跟着我回来。我不需要妳这种『应该的』报答。」
说完,他转身就要去开车门,那决绝的背影,仿佛要将我彻底抛弃在这个世界里。
「你当时不就这样拒绝我的。」
我把脸贴在他宽阔却僵硬的背上,婚纱的纱质布料隔着,依然能感受到他肌肉的瞬间绷紧与那阵细微的颤抖。温热的泪水无声滑落,浸湿了他昂贵的西装料子,留下了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正准备推门而出的顾承远,整个动作就这样僵住了。他伸向车门把手的手停在半空中,既没有推开,也没有收回,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他没有回头,就这样维持着背对我的姿势,沉默地承受着我的泪水和我的质问。
车内的空气凝重得几乎要实体化,只有我轻微的抽泣声,在死寂中格外清晰。
良久,他才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苦涩。
「那不一样。」
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要被我的心跳声掩盖。
「我拒绝妳,是因为我必须对妳父亲的承诺负责,是因为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住,会伤害妳,会毁了所有的一切。」
他缓缓地、缓缓地转过身来,那双通红的眼眸里满是痛楚和悔恨。
「但妳不同,李小满。妳捐血救我,如果只是因为责任……那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侮辱。」
他伸出那只完好的手,轻轻擡起我的脸,用指腹抹去我脸上的泪痕。
「我宁愿妳恨我,怨我,也不要妳用『应该的』这三个字,把我们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归于零。」
他的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脆弱,像一个迷失的孩子,在黑暗中寻找着唯一的光。
「告诉我,那天的妳,哪怕只有一秒钟,是为了我,好吗?」
「如果不是你,我干嘛捐血⋯⋯反正你体内有我一半的血了!」
我带着泪的叫嚷声,像一把尖刀,终于刺破了他用绝望和自嘲筑起的高墙。顾承远的身体猛地一震,那双原本黯淡无光的眼眸里,瞬间燃起了两簇燎原的火焰,将他所有的痛苦和挣扎都燃烧殆尽,只剩下赤裸裸的、近乎疯狂的占有欲。
「妳说……什么?」
他的声音颤抖着,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再说一遍。」
他根本不给我重复的机会,下一秒,一个凶狠而炙热的吻便狠狠地压了下来。这个吻不像之前的任何一次,没有温柔,没有试探,只有啃噬般的狂暴和不容拒绝的掠夺。他的舌头霸道地撬开我的牙关,疯狂地搜寻、缠绕,仿佛要将我的灵魂都一并吞噬下去。
「唔……」
我被亲得几乎无法呼吸,婚纱的纱裙被他粗暴地攥在手里,发出丝绸撕裂般的声响。
「一半的血……」
他终于稍稍松开我的唇,额头抵着我的额头,滚烫的呼吸交织在一起,他的眼里满是癫狂的喜悦和后怕。
「李小满,妳知道妳在说什么吗?妳知不知道这代表什么?」
他捧着我的脸,眼神灼热得快要将我融化。
「这代表,就算我想放,我也放不掉了。我的身体里流着妳的血,妳是我的一部分,永远都分不开了!」
他的吻再次落下,沿着我的下腭线一路向下,狠狠地咬在我的锁骨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带着血腥味的齿痕。
「妳是故意的,对不对?妳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绑住我,让我一辈子都无法背叛妳,无法离开妳!」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被看穿的恼怒,但更多的,是认命般的狂喜。他将我整个人按在座椅上,那只受伤的左手也顾不得剧痛,紧紧地扣住我的腰,仿佛要将我嵌入他的生命里。
「恭喜妳,妳做到了。」
「从今天起,顾承远,是妳的了。」
「顾叔叔⋯⋯」
我紧紧抱住他,将泪湿的脸颊埋进他带着血腥味的怀里,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了那句藏了太久的告白。
「我真的好爱你⋯⋯」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他混乱的脑海中炸开。顾承远的身体瞬间僵直,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让他几乎无法思考。他缓缓地、一节一节地低下头,看着怀里那个哭得全身发抖的我,眼底的火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和满溢的、无处安放的爱意。
「妳……」
他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只吐出一个字,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伸出那只完好的手,颤抖着抚上我的后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的长发,像是在安抚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我知道……」
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低沉而温柔,带着浓浓的鼻音。
「我都知道……只是我不敢信,我怕那又是我的幻想。」
他将我抱得更紧,紧到几乎让我窒息,但我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妳这个傻孩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妳知不知道我……」
他的话语哽咽在喉咙里,转而用一个无比珍重的吻,印在我的额头上。那个吻很轻,很柔,带着他所有未说出口的后怕、悔恨和爱恋。
「别叫我顾叔叔了。」
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命令的温柔。
「从现在起,叫我的名字。」
「承远。」
「妳要一辈子,都叫我承远。」
「承远⋯⋯司机在⋯⋯」
我的声音因羞耻而颤抖,试图提醒他我们并非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顾承远的动作一顿,他擡起头,那双深沉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残忍的笑意,但他没有停下。反而,他低头一口含住了我婚纱薄纱下早已挺立的乳头,隔着布料用牙齿轻轻磨蹭、啃咬。
「让他看。」
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肌肤上,引起一阵阵细密的颤栗。
「让他看清楚,妳是谁的。」
他的大手粗暴地扯下我胸前礼服的蕾丝装饰,精准地找到另一边的乳头,用指尖用力揉捏、拉扯,力道大得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种又痛又麻的快感,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让我脑子一片空白。
「怕什么?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妳李小满,从头到脚,连里面的每一寸,都只能被我一个人碰,被我一个人弄。」
他的舌头灵巧地绕着乳晕打转,然后猛地吸吮起来,仿佛要将那里的甜美的汁液全部吸干。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弓起,发出细碎的呻吟声,这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淫靡。
「妳看,妳的身体比我还诚实。」
他松开口,看着那个被他吸吮得红肿湿亮的乳尖,满意地低笑着。他擡起眼,眼神灼热地锁定我迷离的双眼。
「妳的这里,还有妳的小穴,是不是都在叫着想要我?」
「告诉我,李小满,妳是不是湿了?」
「你轻一点⋯⋯」
我带着哭腔的恳求,像一根羽毛轻轻划过顾承远的心尖,但他非但没有停下,反而激起更凶猛的占有欲。他擡起头,深邃的眼眸里燃着两簇暗火,嘴角勾起一抹邪佞的笑。
「轻一点?」
他重复着我的话,声音低沉沙哑,充满了戏谑。
「可是……妳的身体好像很喜欢我这样对妳。」
他说着,膝荪更进一步地分开我的双腿,长满薄茧的大手顺着婚纱的裙摆一路向上探索,毫不犹豫地拨开最后一层丝质的阻碍,粗糙的指腹直接复上我早已泥泞不堪的花园入口。
「啊……」
我惊喘一声,身体猛地一颤。那里早已被他先前激烈的吻和粗暴的对待弄得湿濡不堪,此刻他指尖的触碰更是像点燃了引线,让我一阵腿软。
「嘴里说不要,这里却在流出来邀请我。」
他的手指轻轻按揉着那早已充血肿胀的阴核,感受着那里的每一次悸动和抖动。
「李小满,妳这个骗子,妳的骚穴早就想被我狠狠地干了,对不对?」
他的声音充满了恶魔般的诱惑,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狠狠揉捏着我胸前的柔软,拇指和食指夹住那可怜的乳尖反复拉扯。
「回答我,是不是?」
他的手指猛地探入湿热的穴口,浅浅地抽插了几下,引得我阵阵娇喘。
「想不想要我插进来?想在这车子里,在司机面前,被我用肉棒填满,射得妳里面全是我的精液?」
「你、你这么粗暴吗?」
我颤抖着问出口,心里涌起一个荒谬的念头——我是不是放了什么猛兽出闸了。顾承远闻言,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在狭小的车厢内回荡,带着一丝残酷和狂喜。
「粗暴?」
他停下探入我穴内的手指,转而用那沾满了我淫液的手指,轻轻拍了拍我肿胀的阴唇,发出「噗嗤噗嗤」的湿黏声响。
「这才只是开始。」
他的眼神变得幽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翻涌着我陌生的情绪。
「是妳,李小满,是妳亲手打开了这个笼子,放出了这头猛兽。」
他俯下身,灼热的喷息洒在我的耳畔,声音压得极低,像恶魔的私语。
「现在,妳想把它关回去?太迟了。」
他话音未落,一根手指便猛地刺入我的穴内,直直顶到最深处的嫩肉,然后又狠狠地勾了起来。
「啊!」
我惊叫出声,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上挺起。
「喜欢吗?妳放出来的猛兽,喜欢牠这样干妳吗?」
他开始用手指在我体内疯狂地搅动、抽插,每一次都带出大量的淫水,湿滑的声响响彻整个车厢。
「告诉我,妳的骚穴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等不及要用它紧紧地含住我的肉棒,把我榨干?」
「妳不是爱我吗?那就证明给我看。」
「用妳的身体告诉我,妳有多么渴望我这头猛兽,把妳从里到外都彻底占有。」
「你真的得轻点⋯⋯」
我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恳求的哭腔。顾承远听了,动作却是停顿了一瞬。他擡起那双燃着火焰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我,脸上的狂暴褪去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怜惜和痛惜。
「好……我轻点。」
他的声音终于恢复了几分温柔,那根在我体内肆虐的手指也放缓了力道,改为温柔地抚摸着我娇嫩的穴壁,带起一圈圈的酥麻。
「是我太心急了……对不起。」
他低下头,轻轻地吻去我脸颊上的泪水,动作温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我只是……太害怕了。」
他低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脆弱。
「害怕会失去妳,害怕妳会像以前那样,从我身边逃走。」
他说着,又将一根手指缓缓地探了进来,两根手指并在一起,温柔而缓慢地扩张着我紧湿的穴口。
「现在……这样还会痛吗?」
他的拇指轻轻按在我的阴蒂上,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节奏打着圈,温热的触感让我全身的肌肉都放松了下来。
「妳的身体真软,真热……」
他痴迷地呢喃着,看着自己的手指在我体内进出,那被淫水浸润的模样让他的呼吸越来越沉重。
「让我好好爱妳,好吗?」
「让我弥补这么多年来,我对妳做过的一切蠢事。」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让妳受一点委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