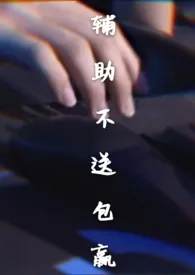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一夜浅眠,脑中混乱的梦境与现实交织,让我分不清自己究竟身处何方。身体的酸痛和疲惫提醒着我发生过的一切,但身旁顾家家沉稳的呼吸声,却又给了我一丝奇异的安定感。
「醒了?」她比我先睁开眼,声音清醒而平稳,仿佛她从未睡过,只是坐了一整夜守着我,「去洗把脸,换上最体面的衣服,我们要去打仗了。」
她的话没有一丝温情的问候,却像剂强心针,让我浑浑噩噩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沉默地走进浴室,镜中的女人脸色苍白,但眼神却不再是昨夜的空洞。我仔细地清洗了脸,画上淡妆,试图遮盖疲态,然后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了那件我刚入职时买的、从未舍得穿的套装。
当我从房间走出来时,顾家家已经准备好了早餐,桌上的托盘里放着两份三明治和两杯黑咖啡。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点了点头。
「很好,就是这个气势。」她将一份三明治推到我面前,「快吃,我们得早点过去,妳要亲手把辞呈交到沈敬禹的桌子上。另外,秦曜森那边,妳打算怎么说?」
我拿起三明治,机械地咬了一口,干硬的面包磨着我的喉咙。提到秦曜森,我的胃一阵抽搐。
「我……」我艰难地咽下食物,「我手机里有他的私人号码,我……发个讯息告诉他就可以了吧?我不敢……再见到他。」
顾家家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让我浑身一颤。她摇了摇头,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不行。发讯息太便宜他了。」她站起身,走到我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按压,「妳越是逃避,他就越能掌控妳。逃避代表妳还怕他,妳的字典里,从今天起,不准再有这个字。」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心脏狂跳。「可是……家家,我真的没办法面对他。他会……」
「他什么都做不了。」顾家家的声音冷静得可怕,「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会在公司里对妳做什么?他敢吗?妳想想他那么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地位,他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妳怎样?」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熄了我一部分的恐慌,却也让我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的残酷。是啊,秦曜森那样的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那副体面的面具。
「去,亲眼见到他,告诉他妳要辞职。」她加重了手上的力道,像是要将力量传递给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妳要让他知道,妳不是他花钱买来的玩物,妳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去留。这是妳夺回主动权的第一步,也是妳报复的开始。」
我机械地将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味同嚼蜡。顾家家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划开了我所有胆怯的借口,露出血淋淋的现实。我没有退路了,如果今天我逃了,就一辈子都只能活在阴影里。
「我知道了。」我站起身,声音沙哑,却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决绝,「我们走吧。」
去公司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就像我过去三十年被消磨掉的人生。紧握着皮包里那份早已拟好的辞呈,纸张的棱角几乎要嵌进我的掌心。一想到待会要见到沈敬禹和秦曜森,我的胃就一阵痉挛。
走进熟悉的大楼,空调的冷气让我打了个寒颤。以往这里是我每天奋战的战场,但今天,我却像个入侵者。周围同事投来的目光,或好奇、或探究,在这一刻都像是尖针,扎在我的背上。
顾家家只是安静地走在我身侧半步的距离,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我最大的支柱。我们没有去自己的办位,直接乘电梯抵达了顶层董事长室外。
「进去吧。」顾家家停在门外,对我轻声说,「沈敬禹由妳自己面对。至于秦曜森,我会在这里等妳出来,妳谈完他,我们就走。」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而昂贵的木门。沈敬禹正专注地看着桌上的文件,连头都没擡。室内弥漫着他身上那股清冷的雪松香,曾让我心跳加速的气味,此刻却只让我感到窒息。
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将那封辞呈平稳地放在他正在阅读的文件旁边。他终于停下动作,缓缓擡起头,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只是平静地看着我。
「什么意思?」他开口,声音平淡得听不出任何情绪。
他的语气平稳得像是在询问天气,但那双深邃的眼眸却像探照灯一样锁定我,仿佛要看穿我灵魂深处每一丝的动摇。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却逼自己直视着他,不让眼神闪躲分毫。
「辞呈,我来辞职。」我的声音比想像中更稳定,或许是因为心已经死了,反而没什么好怕的,「感谢董事长这段时间的栽培,但我决定离开。」
沈敬禹没有去看那份辞呈,他的视线依然停留在我脸上,似乎在评估我这句话的真伪。办公室里的空气凝滞了,墙上时钟的秒针滴答声,在此刻显得格外刺耳。
「理由。」他终于再次开口,语气依旧没有起伏,但这两个字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我没有批准,妳不能走。」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提醒着我这个男人的绝对权威。在这家公司,他的话就是规则。我的心脏猛地一沉,准备好的腹稿瞬间被打乱,但顾家家那坚定的眼神浮现在脑海里。
「这不是申请,是通知。」我吸了一口气,鼓起毕生最大的勇气,「个人原因,我不想再做下去了。至于批准……我想,我并不需要您的批准来决定我的人生。」
沈敬禹的眉头微不可见地蹙了一下,这是他脸上出现的第一丝情绪波动。他没有因为我的顶撞而发怒,反而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形成一种更具压迫感的审视姿态。
「妳的人生?」他重复着我的话,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弧度,「李觅欣,妳确定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的目光缓缓下移,扫过我紧握的双手,又回到我的脸上。「进我的办公室之前,妳想过后果吗?以为辞职一走了之,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重锤敲在我的心上。他没有明说,但我们都清楚他指的是什么。是秦曜森的钱,是贺景琛的纠缠,还是那些不可告人的关系。
「我不懂您的意思。」我强自镇定,但颤抖的声线还是出卖了我,「我只是单纯地不想工作了。」
「是吗?」他轻笑一声,那笑意却未达眼底,「那四千五百万,妳打算怎么处理?秦曜森花了那个价钱,可不会轻易放妳走。」
他轻描淡写地抛出那个羞辱性的数字,像一把利刃狠狠刺穿我所有的伪装。我脸色瞬间血色尽失,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他竟然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一直都知道?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他以一种全知全能的姿态,轻描淡写地揭开了我最深的伤疤,那种被看透、被掌控的恐惧,比秦曜森的粗暴更让我窒息。
「那笔钱,是我给的。」他终于收回那审视的目光,转而凝视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陈述一笔与自己无关的帐目,「秦曜森不过是代为转交。我的授权下,财务才会拨款。」
我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站立不住。原来如此……所以秦曜森才会那么有恃无恐,因为他只是个执行者。真正的买家,一直是我面前这个男人,我十年来仰望的偶像。
「至于周澈安给你的……」他转回头,眼神深处掠过一丝不悦,「我知道你没收。你还不算太笨。」
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指间无意识地转动着,那双眼睛再次将我锁定。
「现在,你还想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