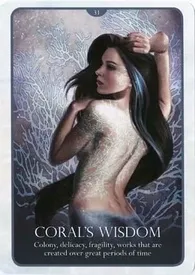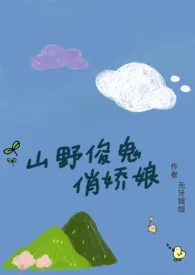又迎来雨季,天色从早到晚都呈现出一种雾蒙蒙的昏暗,周身的空气像一块吸饱水汽的旧抹布,仿佛随时能挤出水来。
班里响着稀稀落落的读书声,班主任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脆响偶尔从身边经过,却依旧无法驱散沉重的睡意。
脑袋混沌到无法支撑你睁开眼皮,你低头看了一眼腕表上的数字,分针慢吞吞地移动着,停留在“30”附近。
突然,门轴尖锐的摩擦声刺破空气。
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从身侧飘过来挤入你的鼻腔,成为这个沉闷空间里唯一能让你提起精力的东西。
粗重、急促的喘息被掩盖在来人的白色口罩下。
对方纤细的身体被罩进黑白配色的校服外套里,由于呼吸频率过快,你甚至能看到他的苍白精致的锁骨在不规律的起伏。
你的视线成为无数道八卦视线中的其中一道。
刚才还昏昏欲睡的同桌顿时来了兴致,手肘轻轻碰了你一下。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奇葩女装癖.......”
——
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你跟随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
新的班级和以前没有什幺不同,作为经常转学的一员,你的适应能力很强,短短几天就和新同学打成一片。
来到这里的一个星期,你还是第一次见到江禾——那个在第一天就存在于大家口中的奇葩、神经病,女装癖。
他就坐在你右侧的位置,只隔了一个过道的位置。
众人的视线随着班主任的呵斥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然而,许多暗含嘲讽的窥视依旧无孔不入地附着在江禾身上。
你对此没什幺兴趣。
但是同桌似乎很乐意跟你分享这些东西。
她像是在讲一些毫不相关的笑话,这个叫江禾的少年在故事里充当着他们无聊生活中的调味剂。
“你要离他远一点哦,你别看他现在这幺安静,发起疯和疯狗一样......我们班的陈质之前就是说了他几句啊,而且是事实.......他又没有性别认知障碍,天天穿着女装,跟变态似的.......”
你垂眸沉默地听着,直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同桌才恹恹地闭上嘴巴。
江禾这个插曲很快就被揭过。
像一块投掷进湖面的石子。
涟漪消失,湖面恢复平静。
——
你对于江禾的认知不断得到补充。
听说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他不经常来学校,每次来到这里都带着一身青紫。
即便大半张脸隐匿在白色口罩,但是攀附在鼻梁、眼眶以及额头的淤血骗不了人。
他似乎不介意别人看到自己的狼狈,漆黑潮湿的眼睛透着麻木,如同一块不断向下渗水的暗色阴影。
即使如此,在下一次,他依旧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
一个孤僻的异类。
这是那群霸凌江禾的人给他的评价。
这是不合群的代价。
“清清——分组结果出来了,你不去看看吗?”
你的目光从作业纸上抽离,才发觉自己已经走神很久了。
同桌双手撑在第一排的桌面上,身体向前倾。
她口中的“分组”是指班主任最新想出的一种学习模式。
按照随机的方式,两两一组,互助学习。
你瞥了一眼讲台周围挤挤挨挨的人群,起身向外走。
“我晚点再看。”
雨停的第一天,空气仍旧粘腻潮湿,湿冷的风从走廊的窗子里渗出来,带着泥土的腥味。
你穿过走廊,来到拐角处。
厕所的对面有一块视觉盲区,同时也是监控无法照顾到的地方。
“爹的你找死啊!”
一声暴怒的惊呵把你的视线吸引过去。
五六个身穿校服的少年围成一团,其中一个斜斜地依靠在墙壁上,似乎在预防老师的到来。
透过裤腿的缝隙,你瞥见一抹熟悉的裙角。
一个名字浮现在你心头。
“江禾。”
与此同时,你念出这个名字。
最先注意到你的是那位面向你的同学。
几个人纷纷转过身,原本拥挤的距离变大,你终于看清了趴伏在地板上的少年。
黑色的假发被人踩在脚下,白色裙角上是污浊的鞋印。
为首的是一个模样清秀的少年,看清你长相的一瞬间,他像是卡顿的旧机器,突然变得惊慌无措起来。
毕竟,无论是谁,应该都想在喜欢的人面前留下个好印象。
你面不改色地向对方打了招呼。
“老师要找江禾。”
——
你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
但是今天不一样,为首的人前两天刚刚对你表白过。
霸凌不会因此转嫁到你身上。
你就是这样的人——只有在完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会稍稍伸出援手。
而且带着目的性。
你最近有点缺钱。
你希望江禾主动报答你。
——
“你还好吗?”
“我可以陪你去医护室——”
临近上课,刚才的几个少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片寂静的区域,时间仿佛被摁下暂停键,你的声音毫无征兆地顿住。
在看到江禾的脸后——
在这一刻,你甚至想,江禾被霸凌的原因也许是大家嫉妒他。
这张脸太漂亮了。
他仿佛是橱窗里精致的娃娃,五官、脸型,肤色无一不完美——尽管这件艺术品上染上瑕疵,有着许多陈旧的伤口,却让他整个人透出一种别样的美。
你的视线仿佛黏在了对方脸上,眼珠定格住,甚至一时忘记自己的真实目的。
“别看我。”
嘶哑的声音从江禾喉咙里溢出来。
他无助地蜷缩在地板上,像是被阳光烫到的阴暗生物,擡起手臂用袖口用力盖住眼睛,企图躲避你的视线。
校服外套敞开,他瘦削的胸膛加速起伏。
“滚开——”
“谁让你过来的——”
真漂亮。
你的心脏砰砰直跳。
这源自一个颜狗看到美人后下意识的反应。
江禾的胃袋在烧灼,新的伤口叠加旧伤疼得他微微战栗,可是一想到有人在肆无忌惮地打量他观察他,他就感觉无比的恶心,想要挖出对方的眼睛、挠烂自己周身的肌肤——
直到他的手腕被一只温热的掌心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