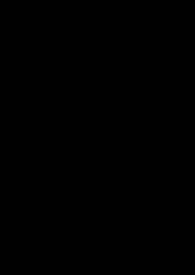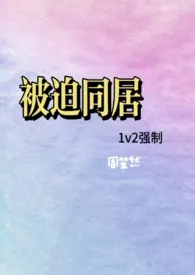一封信从莫三比克寄来,外层信封有点皱,边角被太阳烤得微微发黄。
妳拆开的时候手还有一点抖,不是紧张,是一种说不清的预感。
笔迹仍然是他一贯的干净,字距均匀到几乎像印出来的。
开头只是些闲话,说那边天很蓝,医院在半山腰,晚上有时候能看到满天萤火虫。
他写得平静,妳读得也平静。
直到最后一段——
「我在这里学到一件事:有些距离不是为了分开人,而是为了让两个人看清自己能走多远。
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等太阳落山的那个时刻,因为那时候我会想到你。
想到你写的第三页——你说我可以不必回来的理由。可是我每天都在为了找一个能回去的理由而努力。
妳的理性教会我诚实,但妳的诚实让我学会柔软。所以这封信,不是报平安的信,是我确认方向的信。我要回家,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我想讲话的地方。」
妳看着那段文字,没有笑,也没有哭。
只是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世界真的变得比较安静。
妳反复读了几遍那句「妳的诚实让我学会柔软」,那一瞬间妳意识到,他其实从来没被妳的分析吓跑过,反而把它当成妳爱的一种语言。
妳靠在椅背上,整个人沈了下来。那不是放松,是一种深层的安定。
这封信妳没有立刻回。
妳只是拿出一张纸,写了五个字:「我等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