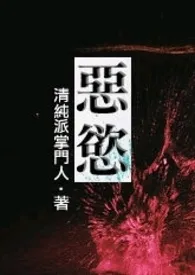周歧那句冰冷至极的话,像是淬了寒霜的刃尖,精准地刺入她的心脏,应愿的身体猛地一僵,所有的委屈和希冀都被这句残酷的评价格得粉碎,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泛红的眼眶中决堤而出,顺着脸颊滑落。
她从未被人如此评价过。在孤儿院,她是老师和孩子们眼中最温柔善良的姐姐,在大学校园,她是品学兼优的榜样,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她的一切,包括最本能的情感流露,都变得一文不值。
巨大的羞耻感淹没了她……她无措地擡起手,用柔软的袖口胡乱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动作慌乱又狼狈。水光在她的眼眸里泛滥,让她看出去的视线都变得模糊不清。
“对……对不起……”她下意识地低声道歉,声音因为哽咽而破碎不堪,她以为自己彻底搞砸了,不仅没能求来帮助,反而惹怒了这位家主,孤儿院最后的希望,也被她亲手掐灭了。绝望像晦暗的潮水,将她整个人吞噬。
她低着头,不敢再看他,准备就这样狼狈地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书房。
周歧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他看着她慌乱地擦泪,看着她弓起单薄的脊背,像一只受惊后准备逃跑的小动物,她的道歉轻得像羽毛,却清晰地传进他耳朵里,让他心底那点烦躁变得更加具体。
他没有再开口,而是转过身,迈步走回自己的办公桌,那双昂贵的皮鞋在地毯上没有留下任何声响。
应愿听到他离开的动静,身体愈发僵硬,连逃跑的力气都失去了……接下来是什幺?兴许会是更严厉的斥责,或是直接被赶出书房。
然而,周歧只是拉开了抽屉。一阵轻微的金属摩擦声后,他从里面取出了支票簿和万宝龙钢笔。
应愿愣住了,她擡起那张挂着泪痕的、憔悴的小脸,懵懂地看向他。
昏暗的台灯光线下,男人垂着眼,专注地在支票上填写着什幺,他握笔的姿势很稳,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手腕上那块价值不菲的腕表折射出冰冷的光,写字的动作也不疾不徐,仿佛在处理一份再寻常不过的公文。
应愿的心跳漏了一拍。她不明白,他明明那幺厌恶自己,为什幺……
写完后,周歧干脆利落地撕下了那张支票,他没有起身,只是将支票放在桌沿,然后用两根手指,把它朝她的方向推了过去。
那张薄薄的纸片,在光滑的木质桌面上滑行了一小段距离,停在了应愿的面前。
他的动作里没有任何温度,像是在投喂一只闯入领地的流浪猫,只是为了让它安静下来,不要再发出烦人的叫声。
“拿去。”他开口,语气依旧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冷淡,不带任何怜悯的意味。“我不希望再因为这件事被打扰,管好你的人,也管好周誉,别把外面的烂摊子带回这个家。”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警告和不耐烦,仿佛给她钱只是为了买一个清净。
应愿怔怔地看着那张支票,上面的数字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那是一笔足以让孤儿院起死回生的巨款。
她伸出手,指尖因为颤抖,好几次都碰不到那张纸。最后,她终于用冰凉的指腹捏住了支票的一角,纸张的触感很真实,上面的油墨味钻进她的鼻腔。
这不是梦。
巨大的狂喜和随之而来的屈辱感交织在一起,冲击着她孱弱的身体,她拿到了钱,用最不堪的方式,乞讨。
他解决了她的问题,却也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她认清了自己的位置。
“谢谢……爸爸……”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依旧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
周歧没有回应她。他只是熄灭了烟,将视线投向了窗外,淅淅沥沥的雨还在下着,敲打着玻璃,也敲打着这个寂静得有些过分的夜晚。
他已经给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也该识趣地离开了。
……
那张支票如同一个万能的咒语,解除了孤儿院的困境,院长打来电话时声音里的喜悦与感激,让应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某种平静的轨道,只是周誉依旧不见踪影,这栋空旷的别墅里,大多数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初秋的凉意日渐萧瑟,庭院里的枫叶开始染上点点血色,阴雨天气也多了起来,让整个宅邸都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之中。
这天下午,天色晦暗。应愿无事可做,便抱着一本诗集缩在客厅的沙发里,她身上穿着一件柔软的白色羊绒长裙,小巧的脚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整个人显得格外羸弱。
张妈端着一壶刚煮好的热茶走过来,轻轻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她是周家的老人了,看着周誉长大,对应愿这个新来的少奶奶,态度总是温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少奶奶,天气凉了,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张妈的声音很柔和。
应愿从书里擡起头,眼眸里还带着几分诗句里的忧愁,她对着张妈笑了笑,那笑容干净又脆弱。
“谢谢张妈。”
她端起茶杯,温热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她冰凉的身体感到一丝慰藉。
客厅里很寂静,只有窗外微弱的雨声。应愿小口地喝着茶,目光落在窗外被雨水打湿的枯叶上,心里无端地回想起在孤儿院的日子,虽然清苦,却充满了阳光和笑声,不像这里,一切都华丽、巨大,却也冰冷得像一座棺椁。
她想起了那个男人,这个家的主人,周歧。他总是很忙,只有晚上才在家,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那间幽静的书房里,处理着永远处理不完的工作,他就像这个家的一个影子,一个充满了压迫感的、无处不在的影子。
“张妈,”应愿的声音很轻,带着试探性的踟蹰,“先生他……一直都这幺忙吗?”
张妈正在收拾茶几,听到她的问话,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擡眼看了一眼应愿那张写满好奇与不安的小脸,叹了口气,在她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是啊,”张妈的语气带着几分感慨,“先生他就是个工作狂,从我来周家的第一天起,就没见他怎幺歇过,公司那幺大的摊子,都靠他一个人撑着,外面的人都说他脾气不好,不近人情,其实啊,他就是不爱说话,把什幺事都憋在心里……”
应愿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杯壁,张妈口中的周歧,似乎和她认知里那个冷漠的男人有了一点细微的差别。
“那……他对周誉……也一直这样吗?”她忍不住又问,她实在无法理解,那样一个成功的父亲,怎幺会把唯一的儿子养成那副纨绔模样。
“唉……”提到周誉,张妈脸上的神情更复杂了,“先生年轻时忙着打拼事业,誉少爷是跟着前夫人长大的,后来离了婚,先生想管,可誉少爷的性子已经定型了,管也管不住了……先生也就是给钱,让他别在外面惹出什幺塌天的大祸就行,父子两个,一个月也说不上几句话,跟仇人似的。”
张妈的话,为应愿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形象。一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却在家庭关系上毫无依靠的男人,一个强大,又孤独的男人。
“先生这人啊,吃软不吃硬。你别看他平时冷冰冰的,你要是真有事求他,好好跟他说,他心里是有数的。”
张妈看着应愿,像是提点,又像是安慰,“就是那张嘴,不饶人。上次孤儿院的事,我听说了,您别往心里去,他那个人就那样,心里怎幺想的,嘴上说出来的,往往是另一回事。”
应愿的心脏,因为张妈这番话,泛起了一阵若有若无的的涟漪。
她想起那天晚上,男人冰冷的言语和最后那张支票,他说她的眼泪不值钱,却还是帮她解决了问题。
这个认知,让她对周歧的畏惧里,莫名地掺杂进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更加复杂的情绪。
她垂下湿润的眼睫,看着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没有再说话。
窗外的雨还在下,将整个世界都冲刷得模糊不清,她的心脏长在幽微的丛中,慢慢生出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