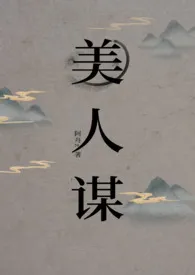关外的天儿,说亮就亮。张家院儿里那棵老榆树枝桠干硬,刺棱棱地戳着刚翻鱼肚白的东边天。寒霜跟撒盐似的铺满青石地面,踩上去嘎吱一声脆响。
吴淮推开西厢角的矮门,一股子凛冽的白气儿呲啦钻进嗓子眼儿,激得他喉咙发紧。他身上那件半旧的靛蓝粗布棉袄裹得紧扎,更衬得个头儿拔得老高,宽肩细腰,像棵风雪里站得稳稳当当的杨树。他搓了搓骨节分明的手,指肚上还留着早起给东家太太担水攥扁担磨的红印子,劲儿是真足。
他擡头望了望主院那扇雕花木窗。那是大小姐张明月的屋。窗户纸还暗着,没透亮儿。他心里却像揣了个小火盆儿,暖烘烘的,又有点空落落的不踏实。
天儿是越来越冷了,道上听说不太平,不知打哪儿流窜过来的几个胡子,专瞅落了单的肥羊敲杠子。老爷太太这两天愁云罩脸的,小姐每日去后街王家绣坊的活儿,也成了心病。
这不,吴淮的差事,也悄悄多了道护送大小姐。这可不是老爷太太吩咐的,是他吴淮自个儿心里那根弦,绷得比张家院墙上的铁蒺藜还紧实。分开超过一天?他连想都不敢想。那是他十三岁那年,顶着个破包袱跟着逃荒的人流进张家门,第一眼就烙在心底的人。在他这块贫瘠心田上,张明月就是最圣洁的仙女,是他心里头唯一的妻子,碰不得,瞧不够,只想揣在怀里捂热乎了。
日头刚爬上墙头,把清冷的亮光抹到张明月闺房窗户上时,那扇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团雪白的影子裹在厚实的银狐皮斗篷里,俏生生地立在了门槛上。张明月出来了。
她个头儿到了吴淮肩膀,乌黑的头发跟泼墨似的垂在腰后,风都没能撩动一根儿。小脸裹在雪白绒领子里,只露半边儿,真真是肤白如凝脂,欺霜赛雪。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黑眼仁儿又圆又亮,真像家里养的那只乖巧的大狸猫,眨巴一下,能滴下水来似的。可那身段儿又一点儿不单薄,斗篷裹着也显山露水,胸口鼓鼓囊囊的起伏,腰那地儿掐得细细一捻,仿佛风一吹就能折了,偏又带着一股子丰润柔软的韧劲儿。这是个天生的尤物,偏生了一副菩萨性子,温婉得像团棉花,又软又怯。
“大小姐,早。”吴淮的声音压得低,带着少年人清爽的底子,又混着点刻意收敛的沉,怕吓着她。他赶紧上前一步,接过她手里提着的沉甸甸的手炉和绣活篮子。目光飞快地溜过她的脸,确认她昨夜睡得安稳,一颗心才落回肚子底。
张明月擡眸看见吴淮,那原本带着点刚睡醒迷蒙的大眼睛,瞬间像落了星子一样亮了起来,浅浅弯成两道月牙儿,脸颊透出淡淡的粉,细声细气地:“淮哥儿,又辛苦你跑一趟。”她身上的暖香,一丝一缕地飘过来,掺着斗篷上狐狸毛的腥气,钻进吴淮鼻腔里,挠得他心头麻酥酥的痒。
后续内容已被隐藏,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