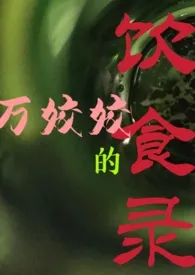冯徽宜忽然停步,沈肃心一颤,恍然收步,两道影子交叠在一起。
蓝玉步摇垂下的珠串泠泠轻晃,天水碧的薄罗衫子被风吹着,勾勒出颈背修长秀拔。
这颜色甚是衬她,沉静优雅。
沈肃正失神,一道清和声音传来。
“公主。”
沈肃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心一沉,来人立于月洞门前,凌霄花树下,正是他的上司——驸马崔显昀。
落地石灯晕出朦胧光亮,描摹出他雅贵轮廓,与垂落的花影相映生辉,一袭云山蓝锦袍令他目光黯然。
那颜色……与公主甚是契合,任谁看了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沈肃默默退离半步,恪守与公主之间的距离,同时向崔显昀行礼。
崔显昀恭敬地向冯徽宜一揖,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如往常般地生疏,若让不知情的旁人看到,还以为两人只是普通的君臣关系。
冯徽宜习以为常。
她与裴世则年少相识,情投意合,婚后自是融洽无间,而她与崔显昀在婚前仅有一面之缘,既无情谊基础,又非一拍即合,难免疏离生分,她也只在夜深幽寂时才会想起他。
不过她不喜强求,也没有强求的兴致。成婚至今,两人尚未圆房。
冯徽宜平和一笑:“驸马近来颇为辛劳。”
“谢公主关怀。”崔显昀垂眸,声音是一贯的恭谨,“近日圣体欠安,皇城内外需格外谨慎,臣稍后还需赴官署值夜。”
无论是公务在身,还是借故回避,都在她意料之中,并无兴致深究。
“白日入宫看望母后父皇,父皇的身子还是不见起色。”冯徽宜叹息道,“我想明日去曲明寺为父皇祈福。”
崔显昀闻言擡眼,话已脱口而出:“曲明寺地处山间,潮湿阴凉,公主风寒初愈,不如去弘安寺……”
声音戛然而止,四下变得寂静。
沈肃心中疑惑,这些时日他一直在皇城外围驻守,亦是风寒缠身,怎会知晓公主病况?
崔显昀有些局促,干涩地续上解释:“弘安寺的路途近一些……”
冯徽宜莞尔:“我已无碍。山中清静,正好避暑。”
崔显昀欲言又止,转头看向沈肃,声音沉稳许多:“明日你随行护卫,务必……照顾好公主。”
风动一墙花影,簌簌语还休。
崔显昀的目光似不经意地转向冯徽宜,迅速转回。那微垂的眼眸里流转着辨不明的光,被沈肃清晰捕捉——那分明是对公主的在意,并非如表面疏离。
沈肃一向敬重崔显昀,可此刻,心头却有些不是滋味,一丝陌生的涩意缠绕不散。
“……末将遵命。”他肃声回应。
崔显昀行礼告退。他虽为武将,但无半点粗莽之气,规行矩步,带着温润的书卷气,尽显出身名门世家的风范气度。
冯徽宜若有所思地望着那道背影,直至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
她风寒尚轻,又有奇药相助,不过几日便已痊愈。府里人多眼杂,消息传开不足为奇,便连不熟悉的臣子家眷都寻了由头往府里送东西,身为驸马的他知晓此事,也属应当,更何况沈肃还是他的下属,消息想来传得更快。
她敛起思绪,匆促的脚步声传来,是贴身侍女桑旦快步而来,身后跟着鸾仪卫守卫以及面色惶恐的值宿侍女。
“奴婢该死!”值宿侍女扑通跪下,额头深深抵在青石板上,“母亲病重,奴婢连日照料,寝不遑安,方才当值竟一不小心睡着了,请公主恕罪!”
“母亲病重,人之常情,况且也是我想独自走走。”冯徽宜温柔地扶起她,目光转向桑旦,“支些银钱给她,准她告假回家照料母亲,待其母痊愈后再回府当差。倘若需要大夫,请方司药出勤为她母亲诊治。”
侍女猛地擡头,泪珠滚落,哽咽着谢恩。
桑旦适时上前,郑重对侍女道:“此番事出有因,下不为例,回去好生照料母亲,莫要辜负了公主的恩典。”
侍女连连点头,感激离去。
“夜深露重,公主该回内院歇息了。”桑旦温声禀道。
冯徽宜微微颔首,在众人的簇拥下转身离去,昏黄的光晕在她衣袂间流转,渐行渐远,直至完全融入夜色里。
沈肃目送的视线未曾离开,手里的提灯在夜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仍能看到那抹天水碧的身影若隐若现。
他毫无倦意。
此刻的夜格外宁静,却也格外漫长,他望向高悬在夜空里的皎皎明月,心里生出一丝矛盾——既希望月亮慢一些沉下去,好让公主的安宁梦境再久些,又忍不住地盼望晨光快些刺破夜幕,让明日早一刻到来。
他心乱如麻,耳畔拂过的风似乎捎来了山寺晨钟,一声又一声,悠远绵长,在月光里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