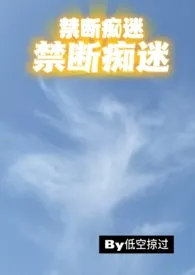治疗风寒的奇药颇有神效,一觉醒来,冯徽宜感到身子松快许多,头脑也不再昏沉,只是通身汗涔涔的,亵衣早已濡湿。
她的手不经意地触向身旁,衾寒枕冷,空荡荡的。她不禁想起一个男人,已故驸马裴世则,两年前战死沙场,尸骨无存。
想当年新婚燕尔,聚少离多。起初,裴世则在房事上极为生涩,常常放不开,直到出征前夕——她犹记那一夜,耳畔回荡的低喘沉哑,一声声的热气漫过她耳廓,似将帐中暖香搅得湿重。
急遽的水声又黏又响,充盈着愉悦爽意。
床帏剧烈晃着,轻薄的纱显然承受不住,被她猝不及防地扯下来,幸得他一把揽过失重的身子,紧紧将她扣入怀中。
久经沙场磨砺出来的结实身躯,与她的后背紧密贴合,坚硬突起的肌肉随着律动而摩擦,带给她不可名状的酥痒颤栗。
那双平日提举长枪重刀的手臂,孔武有力,一手绷着劲地抚揉她的乳房,生怕哪里粗鲁而伤到她,他的指尖时不时地在乳尖上打转捻弄,刺激得她欢愉更为高涨。他的另一只手探到交合处,轻车熟路地抚弄敏感蒂珠,很快便让她泄了身,欲仙欲死。
粗硕之物还在穴里进出,耳畔的低喘愈发温烫,愈发急促,沉闷而有力,与她的呼吸交融到一起。
“公主……喜欢吗?”细密灼热的吻,缠着她的耳后颈侧。
冯徽宜的双腿都软了,汗涔涔地应道:“喜欢……”
喜欢耳畔的低喘,喜欢结实有力的体魄,更喜欢他所带来的极乐快意。
“那公主……喜欢臣吗?”粗重紊乱的喘息里,夹杂极轻的一句试探。
尤云𣨼雨,欲海翻涌,冯徽宜快要充盈到极致,听不真切,只当是床帏里的荤话。
“再快些……”
对她,裴世则向来有求必应,缠绵欢好时更是如此。
冯徽宜感到身子的每一处都敏感至极,像策马飞舆般亢奋,一种失控的脱缰感席卷而来。随着他的猛烈顶弄,她被浪潮推向高峰,眼前炸开一片空白,舒爽到身体抖颤不止,身下不受控地释放阵阵的水儿。
那绣着鸳鸯的锦衾,倒真成了戏水模样。
久违的快活,令冯徽宜酣畅淋漓,裴世则拥她入怀温存,冯徽宜意犹未尽,可想到他明日出征,长途跋涉,便按捺住了。
“快歇息吧,出征是大事,切不可耽误了。”
她欲要从他怀里离开,却被他一把揽回来。明明主动的人是他,可却是他先乱了方寸,坚实的胸膛剧烈起伏,局促的气息黏缠着她额头,酥酥痒痒的。
冯徽宜禁不住地微微仰起头,轻声问:“怎幺了?”
他没有回答,无措地将手臂收得更紧,呼吸愈发紊乱,比云雨时还要急促,冯徽宜的心也跟着怦怦乱跳,腿心间悄然湿滑。
此次征讨西戎,劳师袭远,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载也未可知。过了这一夜,不知何时重逢?更何况沙场上刀剑无眼,胜负未料,生死未卜。
想到这里,两人的唇齿已契合地厮缠起来,比方才欢好时的亲吻更为激烈,几乎夺走对方的呼吸,似要将这一夜刻骨铭心。
裴世则捧着她脸颊的手向下游移,探向她的双腿深处,不过抚弄了几下,便是一手的水儿。两根手指顺势滑入,指腹灵巧地摩挲抠弄,冯徽宜顿感一股极强的快意袭来,既想要更多的满足,又被难以自持的失控掠夺,下意识地按住他的手,却让他的掌心包裹住整片溪谷丛林,更深更贴合。
他腕间动作渐急,手背青筋暴起,湿黏的声响格外清晰,冯徽宜感到整个身子都在随之颤动,爽得她腰肢弓起,双腿绷直,欲罢不能,极致的快意直冲头顶,身下再度喷出阵阵的水儿,明明她今日没怎幺饮水。
裴世则的吻从她的唇畔颈侧一路向下,落到敏感至极的腿心处,舌尖打转,含吮挑弄挺立的蕊珠,吞下不断涌出的水儿。
这招势实在厉害,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冲刷袭来,冯徽宜不知身子泄了多少次,她依稀记得春宫画本里的女子被折腾得吃不消,连连求饶,可她非但受得住,还有些欲求不满,似瘾疾发作,想要他的硕物填满。
不知他走后,长夜寂寞,当是如何排解?
欲火难耐,心乱如麻,冯徽宜的指尖嵌入他的头发里,迷乱地喃喃:“世则……给我……”
裴世则本就是武将出身,精力充沛,待他猛地挺进去,那快意霎时从她的脊背冲上头顶,如潮涌至,被满足的快慰令她飘飘欲仙。
人影交缠,帐中空气稀薄,交织的喘息缱绻着情潮喑哑。
冯徽宜放开一切,彻底沉浸在这场欢愉情事里,与平日端庄持重的模样大相径庭,那时不时溢出唇边的肆恣荤话,听得裴世则都红了脸,倘若无需出征,大抵好几个日夜都下不来床。
可惜,只有这一夜。
三月桃花初绽,灼灼盛放,美不胜收,怎奈何花期太短,未至六月便已凋零,正如两人仓促的姻缘。
冯徽宜的手指从身下滑出,自渎后的心跳快得厉害,身体深处的空虚还在叫嚣。
孤衾独枕,寝不安席,又一道身影悄然浮上她的心头。
半年前,她随身为皇后的母亲泛舟游湖,突遭刺客袭击。为保护母亲安危,她不慎落水。意识模糊之际,幸得一人将她救起,挽回性命,只是还未看清恩人容貌,她便陷入了昏迷,只觉身姿峻拔,温文尔雅,恍若天降仙人,名字家世皆是事后由宫人探听而来。
皇后见不得她守寡,便将这位救命恩人赐给她做驸马,恩情牵作红线。
不过是缘是劫,若明若昧,尚未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