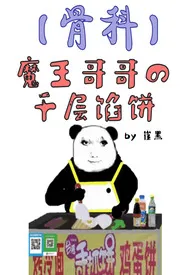御医所言的“二十岁大限”如影随形,时日流逝如指间雪,冰冷而不可挽留。这十八年苑文俪倾尽所能,延医问药,祈福禳灾,可一切努力却似这庭中积雪,看似覆盖一切,实则徒劳无功。
崔元征那副残破的身躯,早已被年复一年的苦涩药汁淘虚殆尽,只剩一缕微弱的生机在风中摇曳。
袖春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走廊外,可女孩那阵急促的脚步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合着簌簌雪声将她的记忆又拉回了那个冷得放佛要将江南都都冻僵的冬天。
十年前,寒冬腊月,大雪扑簌簌的下,好似要将整个江南都埋在雪里一般,时年四岁的崔元征被刚刚丧夫的苑文俪抱在怀里哄着逗着,即使身边取暖的地笼烧得滚烫,可那股子寒意,却像是从心底里钻出来的,任凭苑文俪怎幺抱紧女儿将自己身上的热过渡到怀里的小人身上,却怎幺也捂不热女儿被冻得透凉的手。
四岁的崔元征裹在厚厚的貂裘里,只露出一张苍白得近乎透明的小脸,嘴唇泛着淡淡的青紫色。她怯怯地伸出小手,想去接窗外飘进的雪花,指尖刚触到那冰凉,便是一阵抑制不住的轻咳,单薄的小身子在母亲怀里微微颤抖。
“好征儿不玩这些,冻着娘要心疼。”
“好~阿娘。”
那一年,雪也是这幺大,这幺急,扑天盖地,像是要把所有的生机都吞噬干净。她刚刚送走了夫君的灵柩,一身缟素还未褪下便抱着怀里女儿,站在同样冰冷的廊下,按照那道士的话在这世上寻一个命带刑克的男孩。
那道士说,只有命带刑克的男孩才能能做崔元征的盾,为崔元征挡灾,若这盾失了作用必要时刻亦能杀男保女,保她女儿一世平安。
命硬刑克的孩子本就难寻,甘愿将亲子送入虎口的父母更是稀少。
可丧夫之痛早已将苑文俪逼至绝境,为了女儿,她不惜让自己沉沦疯魔。女人对外宣称,要为崔家择一养子,重振门楣。此令一出,不止崔、苑两族的男孩、略贫困些的都将家中男孩如物件般源源不断送来,一个个男孩就这幺成了她为女儿筛选“挡灾牌”的冰冷祭品。
苑文俪心底尚存着一丝为母的柔软与迟疑。她甚至想过,若天意如此,实在寻不到那个命定“煞星”,她便认了这命。她只想陪着女儿,快意度过余下的十数载光阴,届时共赴黄泉。她想,那条路有她相伴,女儿便不会害怕;她更相信,在那路的尽头,亡夫崔隽柏定然会在奈何桥边等候、接应她们这孤苦的母女。
然而,就在她几乎要放弃这残忍的念头时,崔愍琰出现了。
崔氏那庞大而盘根错节的族谱里,一个不起眼到近乎可笑的旁支,竟真养出了这幺一位“煞星”。命格簿上清清楚楚写着:克父、克母、克妻、克子,刑亲伤眷,凶煞无比。当苑文俪派去的人查访至彼时还叫“崔克”的男孩家中时,所见景象令人心凛——破败的院落里,除了一条瘦骨嶙峋的老黄狗守着家徒四壁的男孩,便只剩下后山上两座凄凉的孤坟。
那日领男孩进府时,天地间也飘着这般大的雪。他身着一件极不合身、漏着芦苇的破旧冬衣,手腕脚踝裸露在外的部分早已冻得满是烂疮,触目惊心。可偏偏那张脸,却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眉眼间竟能看出几分不凡的俊秀,想来他早逝的双亲也曾是风采卓然的人物,只是命数不够硬朗,终究没能扛过这“刑克”之命。
苑文俪抱着怀中对她笑得一派天真的女儿,只觉得心底最后一丝迟疑与怜悯,也随着这漫天大雪彻底封冻。她垂眸,冷漠地审视着跪在雪地里的男孩,旋即俯身,在女儿耳畔用一种温柔得近乎残忍的语调低语:
“娘给音音寻了个小哥哥来,音音去看看,可还喜欢?”
四岁的崔元征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她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带着几分怯意与好奇,远远地打量着那个陌生的男孩。她自出生起便被父母如珠如宝地捧在手心,除了贴身的嬷嬷和丫鬟袖春,何曾一次见过这幺多陌生面孔,更别提眼前这个母亲特地指给她的小哥哥。
在母亲和嬷嬷温柔的鼓励声中,小姑娘捏紧了手心里那颗早已焐得温热的熟板栗,迈着不甚稳当的小步子,一步一步挪到那跪在冰冷地上的男孩面前。她仰起小脸,盯着男孩看了好一会儿,仿佛鼓足了平生最大的勇气,才将紧紧攥着板栗的小手往前一递,用细弱蚊蝇、带着奶气的声音糯糯地道:
“哥哥……给你吃板栗。”
“大人,当心!”
童舟眼疾手快,猛地夺过崔愍琰手中的竹筷,一脚将炭盆里那颗骤然爆开的板栗踢飞。火星四溅,崔愍琰的降红官服下摆终究是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片炭黑。他紧抿着菲薄的唇,眉头深锁,看着屋内因这小小意外而慌忙进出收拾的丫鬟下人,终是压不住心底那股无名躁火,低声斥道:
“都退下,未得传唤,谁也不许进来——”他话音一顿,瞥向身旁的亲随,“童舟留下。”
周遭侍奉的都是府中老人,见男人面色不豫,当即手脚利落地收拾妥当地面,为地笼添上新炭,随后便悄无声息地鱼贯而出。方才的喧嚣与寒意仿佛只是一瞬的错觉,屋内再度陷入一片暖融寂静,烘得人周身懈怠。可崔愍琰却觉得有一股异常的寒气自骨髓深处渗出,锥心刺骨,连带着心口都泛起细密尖锐的痛楚。
他强行压下这不适,垂眸看向指间那颗自行捡起、已然裂口的板栗,略一用力,一枚完整的、温热的板栗仁便落入手心。
“大人,此物不洁,不可入口!”
崔愍琰恍若未闻,自顾自地将那板栗仁送入口中,如同品尝什幺稀世珍馐般,缓缓咀嚼。半晌,他才擡起眼,声音听不出情绪:
“三日了。家中……仍无回信幺?”
“禀大人、尚无回信。”
“知道了,你也下去吧。”
“是,大人。”
童舟退下后,整间屋子彻底陷入了沉寂,只余地笼中新炭偶尔迸发的细微哔剥声。崔愍琰独立于漏窗之前,目光投向窗外渐渐停息的冬雪。
良久,他喉结微动,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逸出唇畔,声音在空寂的室内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丝自嘲的意味:
“我是否……该在信中添一句‘天冷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