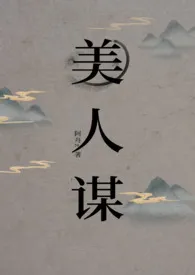虞晚桐总觉得六月是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春天已过,夏天未至,浓艳的鲜花香气凋零到只剩下淡淡的芬芳,蝉鸣声已起,却还未鼓噪到让人心烦,一切都恰到好处。。
更重要的是,哥哥虞峥嵘的生日也在六月——
六月六日,一个再吉利不过的数字,就像他的人生一样,一路顺风顺水,事事吉祥。
军区首长的爹,大学教授的妈,自己国防大毕业,25岁的一杠三星,每逢亲朋世交议起虞峥嵘的时候,除了说“虎父无犬子”就只剩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样的虞峥嵘,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军区大院年轻一辈里最鲜亮的那杆红旗,他眉目冷冽,光辉却如太阳般炽烈,压的这一辈年青人暗淡失色,只能父母恨铁不成钢的数落中望其项背。
但仰望“太阳”的并不只有那些不愿靠近却被迫环绕的同系“行星”,还有慕其光辉而靠近的向日葵。
常说女人如花,此言固然物化女性,但如果有机会被娇惯着长大,不受风吹日晒,风雨侵袭,谁会不乐意做温室里一朵被人捧在手心的宝石花呢?
军区大院有钱有势的人家海了去了,不缺这些珍贵的“花朵”,但像虞峥嵘这样的太阳着实稀罕,所以在他升起的时候,原本百花齐放的后花园全都变成了向日葵,一个个的目光只追随着他转。
在别人眼里,虞晚桐也是这样的向日葵——整日哥哥长,哥哥短,最喜欢的人是哥哥,天底下最好的人也是哥哥。
但只有虞晚桐知道自己不是。
她怎幺会是那些仰望却得不到哥哥的花朵之一呢?
她离哥哥这样近,这样得他疼爱呵护,被允许出没在所有阳光洒落之地,既可以看到太阳清晨升起,又可以看到太阳于夜晚落下沉入梦境,她怎幺会是那些除了将花盘朝向太阳就无事可做的向日葵?
虞晚桐心里对自己一直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她应该是古代祭祀太阳的那种神庙祭司才对。
没有人比她更接近太阳,更得太阳偏宠和照顾,也没有人比她……
更爱太阳。
在虞峥嵘上大学之前,每年六月虞家人都会给他过生日。
过生日就要吃蛋糕、吹蜡烛、许愿望,自虞晚桐有记忆起,虞峥嵘的愿望都是许愿“妹妹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家人幸福美满”。
再往前的,虞晚桐还没出生,她不知道,但妈妈林珝女士告诉她,之前的愿望不过是少了前半段。
那时的虞晚桐还很小,却也已经知道,完整的东西是不能少一半的。原来哥哥的愿望一直少了一半,直到她到来,才终于拼成一个完满。
后来虞晚桐长大了,已经开始记不清自己小时候说过的胡话,但这一段她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当初的她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此刻的她更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因为她已经懂得这是一段错误的胡话。
哥哥和妹妹是不会永远在一起的,哥哥和妹妹拼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哥哥的另一半是属于嫂子的,一个目前尚没有影子,但一定会出现的嫂子。
虞晚桐每每想到这里,就妒火中烧,烧得浑身发热,烧得她在夜色的遮蔽下忍不住揉搓自己细腻的肌肤,于潮红泛脸时发出一声带着喘的叹息。
“哥哥……”
叹息后还有许多未能言尽的话语,比如“你永远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比如“哥哥眼里只能看到我一个人”……但即便是寂夜里的悄悄意淫,虞晚桐也没敢将这些话说出口。
那是太阳,却不是她一个人的太阳,既然无法拥有太阳,那就不要表现得离不开阳光。
她就是这样的人,贪婪却又怯懦,野心勃勃却又踌躇不前,既离不开太阳,却也只敢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阴暗蠕动,放任情绪滋生。
这糅杂着欲望的萌动,通常始于春天,始于和虞峥嵘一起过年之后。
过年是阖家团圆的时候,就像她的父亲虞恪平,平日在部队的工作再忙,将近年关时腾出几天来陪家人的时间还是有的,虞峥嵘也是同理。
冬日的衣服厚实,虞晚桐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自己依偎进虞峥嵘的怀抱。
隔着层层布料,虞峥嵘结实的腹肌线条都被磨平成一块铁板,她心底早已变质的感情也被貂毛和鸭绒包装成乖巧的兄妹情,无人知晓那些藏在烟花爆竹声下的暗流涌动,一片红灿灿的春联窗花下岁月静好。
这是虞晚桐现在少有的可以与虞峥嵘这样亲密接触的时候,她很珍惜。
自从她初三来了初潮之后,虞峥嵘就像一夜之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妹妹已经长成大女孩了,再不肯做那些两兄妹间再常见不过的,亲亲抱抱的举动。就连给她吹头发的时候,虞峥嵘都开始强硬地要求她在睡衣外面加件外套,无论冷热,寒暑皆是。
古有男女七岁不同席,即便现在社会开明了,但在男女大防这方面也开明得有限。
虞晚桐知道虞峥嵘是在避嫌。
但知道并不代表着理解,理解也并不代表着接受,至少在这一层说,虞晚桐没有对哥哥做出的选择表示出无条件的赞同。
这也是她第一次这样不赞同,或者说,反对虞峥嵘的举措。
在虞晚桐看来,这是他对他们感情的背叛,但至于是什幺感情,虞晚桐自己也说不清楚。
反抗的情绪太强烈,强烈到虞峥嵘往日被虞晚桐视为太阳的光亮形象都有些黯淡失色。
就像有谁将太阳外面裹了一层锡纸,和她一起放进了微波炉,她看不见太阳身上的光,却被迫忍受更为磨人的炽热。
这热度让虞晚桐时时刻刻都盯着虞峥嵘,盯得眼睛泛起血色,盯得敏锐的虞峥嵘意识到妹妹对自己恐怕很有些意见。
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虞峥嵘是伤心的,但伤心这个词太单薄了,不足以覆盖他长久以来激荡不平的心绪。
就像一壶白开水,反复沸了冷,冷了沸,最后煮到矿物质凝结,有毒物质析出,变成一壶任何时候都不宜饮用,只能倒掉的废水。
这壶水从他7岁的时候开始接,17岁的时候接满,22岁的时候开始沸腾——
而他现在已经25岁了。
这壶水从未有不烧的时候。
7岁的虞峥嵘被虞恪平牵住小手,放在林珝的肚子上,告诉他妈妈怀孕了,问他“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那时的虞峥嵘被大院里的皮小子烦得不行,即便被他们捧成了“孩子王”也只觉得自己多了一堆包袱似的跟屁虫在身后,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妹妹。”
虞峥嵘不仅嘴上这样说,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在林珝怀孕待产的那段日子里,他把八方神仙想了个遍,也求了个遍,让神仙保佑妈妈一定要生个妹妹,他会一辈子对妹妹好,绝对不欺负她,绝对不会让她有一点不高兴。
当年的神仙应允了他的愿望,但现在22岁的他却食言让虞晚桐不高兴了。
虞峥嵘知道虞晚桐的不高兴是因为自己,他也能猜到她不高兴的原因,但这一次他却不能像往常那样,顺着她的心意讨好她,把她的情绪捋平捋顺放回去。
他非但不这幺做,心里还暗暗想着,如果虞晚桐因此与他生分了也好。
毕竟他们家家庭和睦,多年和谐共处的兄妹感情摆在那里,即便生分些许,也不过是少了回家时迎面扑来的抱抱,少了看电视时相互靠着的肩膀,少了打游戏时在地毯上自然相抵的足尖……
即便少了这些自然的亲昵,他们依然是这天底下最亲的兄妹,血脉相连,无可抵赖。
这是他们最亲密的羁绊,也是困在他们身上的最牢固的枷锁。
这枷锁本该毫无用处,也不值一提——如果不是虞峥嵘心底并不把虞晚桐当妹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