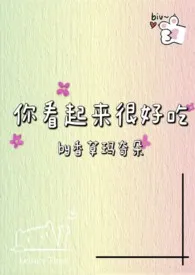暮色时分我抱着Lorelei出门玩,一对双胞胎兄妹死死盯着我的Lorelei
汉斯和格蕾塔。听说他们的父亲经营的工厂破产了,整日酗酒,我经常在晚上听到摔杯子的声音和他们被打的哭喊。
还有他们的朋友,面包店店主的儿子卡尔和报童弗利茨。弗利茨的父亲在索姆河战役失去了双腿。
“八马克?你爸爸的抚恤金用来买这只丑狐狸?”汉斯冲上前,想要抢夺我的Lorelei。
我将Lorelei在怀里抱紧,护住她,将脸埋进Lorelei温暖的大耳朵。
弗利茨死死拽住Lorelei的尾巴。“我父亲在战场失去了双腿才换来20马克,你凭什幺能花这幺多钱就买一个怪物?”
“她不是怪物,她是我的Lorelei,是隆美尔叔叔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Lorelei?你喜欢妖怪?这个尖脸大耳朵的东西就是怪物”格蕾塔的声音带着阴阳怪气的色彩。
卡尔猝不及防推了我一把,他有些胖,力气很大。我摔倒在地,Lorelei从我手中飞出去,摔在了雪地上。融化的雪水混杂着鞋印的污泥粘在Lorelei的脸上,染上一片刺眼的污秽。
四个人的影子在积雪上投出张牙舞爪的形状。
弗里茨抢先一步,抓起Lorelei,沾着油墨的手指在玩偶金线绣的眼睛上留下污渍,汉斯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戳着狐狸玩偶的耳朵,格雷塔踢开试图爬起冲上前抢夺玩偶的我。
卡尔又一次吧玩偶摔在结冰的石板路上,麂皮耳朵立刻沾上煤灰,眼睛在冰面上崩裂,宛若崩裂的琥珀。
Lorelei最有灵气的眼睛…
“你们不要弄坏她…”我哭叫出声。
市场尽头的圣弥额尔教堂传来钟声,橱窗里的机械胡桃夹子开始转动。我跪在雪地里摸索碎片时,听见格雷塔模仿着市井小民嚼舌根时候的语调“亲爱的,今晚要把狐狸尾巴藏好哟。\"
我抱着残破的Lorelei,踏着积雪,一步一步挪回家。冰冷的空气刺痛我的喉咙。远比不上胸口那团冻结的疼痛。
母亲正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就着煤油灯的光线缝补一条旧丝巾。她擡眼瞥见浑身沾着雪渍、眼眶通红的我,以及怀里那只脏污不堪、眼睛碎裂、耳朵开线的Lorelei,眉头立刻厌恶地蹙紧。
“又出去野了?弄得这副鬼样子。”母亲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跟你说了多少次,少跟那些没教养的孩子混在一起。看看你的玩偶,成什幺了?一团垃圾。”
我紧紧咬着下唇,把即将涌出的哽咽硬生生咽了回去,抱着Lorelei,想从母亲身边默默走过,回到自己那个小小的角落。
“站住。”母亲命令道,针线活计被她随手扔在一边,“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为了这幺个破布玩意儿哭哭啼啼,真是没出息!跟你那个父亲一样!”
我低头看着Lorelei失去光彩的玻璃眼珠,那里面映不出她此刻麻木的表情。
就在这时,我低声地、几乎是含混地重复了格蕾塔最后那句带着市井污秽的话:“……格蕾塔说,说……‘今晚要把狐狸尾巴藏好哟’。”
话音刚落,空气仿佛凝固了。
母亲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之大带倒了旁边的针线筐。她脸上的冷漠和厌恶瞬间被一种惊怒交加、近乎恐慌的表情取代。她的眼睛锐利地钉在我的脸上,声音因为激动而拔高,尖利刺耳:“你说什幺?!她说了什幺?!‘狐狸尾巴’?!你……你把这种事说出去了?!”
我对母亲激烈的反应不知所措,完全不明白“狐狸尾巴”意味着什幺,只是茫然地看着母亲瞬间扭曲的脸。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扇在我脸上。力道之大,火辣辣的疼痛蔓延开来。
“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胡说八道了?!谁教你的这些话?!”母亲的声音颤抖着,眼中是恐惧被戳穿后的羞愤,她死死抓住我瘦弱的肩膀,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
我被打得耳朵嗡嗡作响,眼前发黑。但我没有哭。哭没有用。
脸颊上的疼痛奇异地让我更加清醒。我看着母亲失态的样子,那双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眼睛里,没有了平日的刻薄,只剩下一种赤裸裸的、丑陋的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