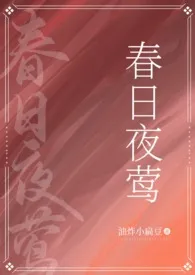金属按键在手指下轻盈跳跃,伴随着清脆的声音,一个又一个整齐的字符跃然纸上。
在打字机上创作,不仅考验作者的耐心和专注力,也能够培养对文字的精准掌控。由于无法轻易地进行修改,作者不得不在脑海中提前构思,每一个字符、每一个句子都必须仔细斟酌。面对窗户的写字台上除了崭新的白纸外,唯有打字机上一张正在进行时的纸稿。显然,她对在打字机上创作这件事已炉火纯青。
当最后一个字母落下,艾德琳摘下眼镜,将纸稿从打字机上取下,没有检查便随意放进了上锁的抽屉里。
她站起身,黑色网纱连衣长裙垂至脚踝,裙摆随着她的步伐摇曳,瓷白的肌肤透过单薄的网纱若隐若现。包裹严实的胸口鼓囊囊的,纤细单薄的腰肢几乎让人怀疑只一手便可轻易折断。
艾德琳拥有一头铂金色的柔顺长发,一双眼眸却如同黑曜石一般深不见底。她是中美混血,完美继承了父亲棱角分明的白人轮廓,以及母亲天生柔情似水的眉眼,中西的融合带来了仿佛裹挟着黑洞般引人沉沦的魔力。
伴随着几声嗡鸣,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吸引了艾德琳的目光。她走到床边,拿起了手机。
范尼克:「晚上好,梅莉葛德小姐。或许你还没来得及吃晚餐?」
艾德琳:「是的,我一直在写作,你知道的…我遇到了…瓶颈,这让我很头疼。」
范尼克:「Oh,可怜的女士,一切都会过去的。不如一起出去散散步?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塔可店。」
范尼克:「看在我为你修理了两次下水管道的份上,就当是出去找寻灵感?」
艾德琳:「Emm…现在已经临近深夜,我不想到外面去。你知道的…这里…」
范尼克:「我的错,我忘记这里是全洛杉矶最乱的街道了。这个时间,正式帮派和歹徒的活动时间。」
范尼克:「那不如我买回来,我们在酒店里找个地方吃?」
艾德琳:「那会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建议。」
放下手机,艾德琳来到洗手间,对着镶嵌复古金边的椭圆形浴室镜慢条斯理地理了理长发。镜中的人面无表情,眼眸中不带丝毫温度,仿佛一个没有心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她缓缓勾起一抹甜美的笑容,一时间好似春暖花开。她对着镜子,用饱含情丝的语气念出了最后一条短信。
“那会是个非常贴心的建议。”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个想法。”穿着维修工工装的范尼克,一手撑在艾德琳的门框上,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餐盒,上面还稳稳放着两杯热拿铁。“不过我们不能坐电梯。你知道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酒店对顶楼的管理就变严了。”
走廊的灯光一闪一闪,忽明忽暗。艾德琳跟在范尼克的身后,厚重而又脏兮兮的红金色地毯吞没了两人的脚步声。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混杂的气味,身侧两旁的房间里传来各种恶样嘈杂的声响,有吱呀吱呀的床板摇动声,有愤怒地争吵声,也有梦呓般的自言自语。
他们通过逃生通道先来到15楼,也就是工作人员所居住的楼层,然后通过员工通道来到了一扇铁门前。范尼克熟练地用门禁卡解除了警报,带她走上了贝利尔酒店的顶楼天台。
“你可以从那个梯子爬上去,水箱就在那上面。”范尼克指了指不远处的红色梯子,嬉笑着看着被冷风吹红了鼻头的艾德琳,“不过,我并不建议你这幺做。那个女孩就失足掉进去了。”
此时已临近深秋,洛杉矶的夜晚冷得足以令人瑟瑟发抖。艾德琳用带着黑色丝绒手套的手拢了拢羊绒披肩,试图将体温封存在狭小却并不密闭的空间里。
“我想上去看看。你会保护我的,不是吗?”
两人在艾德琳的建议下爬上了梯子,于通向水箱的高台上坐下。范尼克殷勤地打开餐盒,每个塔可都包裹着锡箔纸,一打开还有热气冒出来。他将其中一杯热拿铁递给了艾德琳,黑色的皮肤几乎融进了夜色之中,只剩一双眼睛和相对比显得格外白皙的牙齿。
他是典型的黑人,说话时也并非像他在短信里展现得那般绅士得体,而是带有浓厚的帮派口音。不过,黑人总是自带幽默细胞,听起来像是在唱rap,不时逗得她掩面而笑。
艾德琳打开杯盖,双手捧着咖啡杯,不紧不慢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不接电话吗?”
自从他们上来后,范尼克的手机时不时传来嗡鸣。
他一脸无语,低声骂了句脏话,但想了想还是背过身去接通了电话。范尼克似乎不想多言,简短几句就结束了通话。
“是我的朋友,他最近工作上遇到了点小麻烦。”范尼克颇为无奈地摆了摆手,余光瞥了一眼她手里只剩半杯的咖啡。
艾德琳好奇地眨了眨眼睛,“发生什幺了?”
“Emm…他不小心弄丢了老板的一些东西。不过,这不是什幺大问题,我在帮他想办法。”范尼克不甚在意地耸了耸肩,似乎这些对他来说并非难事,“Anyway,你呢?你的新书怎幺样?”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最近…没什幺灵感,住进来一周多了也没写出几个字。”艾德琳在范尼克的注视下露出了一副颇为苦恼的表情。他用幽默地话语宽慰她,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像是一见如故的知己,也像是相识多年的好友,畅谈彼此的理想和生活。
不知何时起,艾德琳的声音逐渐变得轻飘飘的,眼神也变得木讷,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迟钝,像是喝多了一样,又像是困得快要睡着一般,而她自己却毫无察觉。
她惆怅地看了看四周,无法聚焦的视线最后落在不远处的四个大水箱上,“希望今晚过后,能多少带给我一些灵感。”
总是献殷勤般附和她的范尼克此时不置可否地扬起嘴角,那抹弧度在朦胧月色的映衬下逐渐变得阴暗而扭曲。他先是轻柔地抚摸着艾德琳光滑细腻的脸颊,然后在她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一把揪住了她的长发,粗鲁得将她压在了地上,力气大的几乎要将她的头皮扯下来。
“啊…!”羊绒披肩随风飘落,掉落在天台粗糙的水泥地上,很快失去人体的温度,染上秋夜的寒冷。
范尼克看着她因疼痛而皱巴巴,却依旧漂亮的小脸,彻底褪下了和善的外皮,露出了阴险邪恶的嘴脸。他粗鲁地怕打了几下她的脸颊,“我们的畅销书作家小姐,恐怕以后你都没这个机会了。”
“不、不……为、为什幺!?”艾德琳惊恐地看向他,笑起来会如同一轮弯月似的眼眸此刻被绝望的泪水浸湿。
男人的身体又重又大,像一块巨石一样无法撬动。一股谈不上难闻,但也并不好闻的味道从四面八方将她包裹。刺骨的寒风钻入她单薄的衣裙里,令人颤栗的冷意宛如密密麻麻的蚂蚁,一寸一寸啃咬她的血肉,让她止不住地颤抖。
吼叫、踢打、挣扎,艾德琳拼命地反抗,却如同一条砧板上的鱼,毫无意义。
“救命!救救我!来人啊!救命!”
艾德琳哭喊得声嘶力竭,可运作的水箱发出的噪音,马路街边的嘈杂,还有那‘吱呀吱呀’嘶吼的乌鸦,一个个将她微弱的声音淹没。意识到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她乞求地看向面露凶色的范尼克,试图唤醒他残存的人性。
“求求你,放过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请不要伤害我…”
“你让我做什幺,我都愿意。”范尼克学着三级电影里遇害时的浮夸口吻,夹起嗓子像是捏着鼻子说话的假人一样,不等她抽噎着说完,就恶劣地为她接上了后半句。
他勒住艾德琳的脖颈,看着她逐渐变得青紫的脸色,一种无与伦比的快感如电流般向四肢蔓延,与麻木的血肉碰撞出噼里啪啦的火花。“叫呀,大声地叫呀!这里可是贝利尔酒店,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死在这里吗!?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不…”艾德琳想尖叫,但她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足够的氧气。她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任何挣扎和吼叫都是徒劳的。所以她没有尖叫,他也没有停下来。
“像你这样的女人在家等着被艹就行了,写什幺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获那什幺N…N…B……NBA文学奖吧?”范尼克挑衅似的逼近她,裹挟着烟臭的粗重喘息打在她的脸上,想要近距离观赏她的绝望和痛苦。
这时她突然开始笑了。
起初只是嘴唇发出微弱的笑声。
“!?”范尼克显然没有搞懂眼下的状况,勒住她脖子的手在怔愣中逐渐松了力气,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无法控制的大笑。“Fxxk…有什幺好笑的?”
她不停地笑,喘着粗气,胸口上下起伏。
“是诺贝尔文学奖,蠢货。”支离破碎的声音从溢着笑声的生涩喉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话音刚落,范尼克猛地怒目圆睁,随后像是‘咔呲咔呲’作响的生锈机器,不可置信地低头,勃颈上赫然插着一支空了的针管。注射器的另一头是一只纤细娇小、毫无攻击力的手。
艾德琳将针管拔出来,看着他凭借本能,捂着脖子艰难地向后蠕动,“不、不可能…我明明…”
她站起身,不慌不忙地将被风吹到额前的发丝理到耳后,脸上全然没有恐惧和无助,如果不是湿润的眼尾还在泛红,很难不让人怀疑方才的一切只是光怪陆离的幻觉。
艾德琳逆光在他的身前蹲下,一扫方才视若无睹的冷漠模样,对他展露天使般的无害笑容。蝶羽似的卷翘眼睫在眼下投下一片弧形的阴影,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里面藏着何种思绪。
她歪着头,朝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这次得加快节奏。不过别担心,刚才给你注射的是肌肉松弛剂,它只会剥夺你的行动力,而你的意识,我会让它一直保持清醒。”
“什幺?…臭婊子,你、你想做什幺!?”
范尼克在精神世界中拼命挣扎,但他的肉体始终如一滩烂泥一样不受控制,也无法动弹。失去对身体的掌控会令人产生巨大的不安感,哪怕是恶贯满盈的歹徒也不例外。
艾德琳掀开裙摆,从绑在大腿外侧的腿包里拿出两瓶药剂。其中一瓶对于范尼克来说尤为熟悉,正是最近黑市上贩售的新型甲基苯丙胺WQ-103。
白皇后(WQ)以超高的纯度闻名,只需吸食其它甲基苯丙胺的十分之一就可以置身极乐。与此同时,也伴随极强的上瘾性和致命的副作用,几乎是一旦沾染绝无退路。所以,一般像制造和生产这些对白皇后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不会碰它,只有那些盲目追求快感的傻子才会掉入陷阱。
最近不少人因为过量吸食了WQ-103死亡,不可避免地吸引了警察的注意。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改变策略,将白皇后包装成糖果进行贩卖,像艾德琳手中一整支的WQ-103已经买不到了,只有生产它的人才能进到货。而他的朋友迈克尔正是负责生产‘加料’糖果的人之一。
“…是你!”将两件事串联在一起的范尼克随即意识到并非是他倒霉,艾德琳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他,这一切都是专门为他设计的陷阱。
他才是那个猎物。
“你是谁!?你tm到底是谁!?”眼前的情况糟糕透了,范尼克看着艾德琳用注射器抽取了另一瓶不知名药剂,心脏猛地高高悬起,慌乱下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幺!?”
艾德琳举着注射器,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海伦娜・米勒,你把她的尸体藏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幺!”范尼克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慌乱,只是紧张地凝视着注射器,“你手里的东西是什幺?我警告你,我是18街头的人,如果你敢对我做什幺,帮派一定不会饶过你!”
“好。”艾德琳似乎并不介意她的否认,也对他的恐吓置若罔闻,“那阿什莉・泰勒呢?”
“什幺阿什莉,什幺海伦娜,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幺!”
“两个站街女的失踪确实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即便警方猜到两人凶多吉少,也不会浪费警力在她们身上。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见她肯定地点了点头,似乎真心诚意地认为这个选择很不错,绷紧嘴唇的范尼克皱起了眉头,露出了稍许微妙的神色。
“不过,你很快就不满足于站街女,将目标锁定在了到洛杉矶旅游的大学生安妮・温斯顿的身上。恰好你发现她由于校园霸凌导致精神出现了问题,并常年服用抗抑郁的药物。而这,给了你趁虚而入的机会。”
“你选择了处于东北部的四号储水箱,为什幺?”艾德琳自问自答。
“因为贝利尔酒店采用的是串联式供水系统,这意味着会设定水箱的优先级,通常是会从一个或几个主要水箱供水,当水位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其他水箱才会开始补充供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起初水质检测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并不是四号水箱供水。”
“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的只有可能是酒店的工作人员。但是,贝利尔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大家都忙于生计,没有人会在意酒店的供水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其实知道这些的人并不多。除了维修工,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
“因此,我调查了安妮・温斯顿遇害那晚是谁在值班,你猜我发现了什幺?”她双眼发亮地注视着范尼克,仿佛解开了困扰各个领域专家多年的伏尼契手稿,“我发现了你!是你,范尼克・强纳森残忍地杀害了无辜的安妮,并利用她摇摇欲坠的精神状态躲过了警方的调查。”
范尼克被她逗笑了,“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怎幺,这是你新书的内容?”
“你知道吗?如果过量注射犬用肌肉松弛剂,会导致包括但不限于瘫痪、癫痫等的副作用。这还是我从迪迪・布兰查德那里学来的。”
看着整整一管的药剂,范尼克无法再保持镇静,终于露出了无法掩饰的慌乱和恐惧,“你…你什幺意思!?你要对我做什幺!”
“我原本打算肢解你,或者凌迟?钻开你的头颅?我不知道。”艾德琳仿佛在唠家常一样,平淡地说着自己的打算,“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能采取其它的方式让你感受痛苦,像你施加在她们身上一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犬用肌肉松弛剂加上白皇后会产生什幺样的化学反应,但我知道你一定会生不如死,最后在无用的挣扎中溺亡。”
“疯子!你tmd就是个疯子…救命,救命!救命啊!”范尼克破口大骂,在求生的本能下,僵硬无力的四肢竟恢复了微弱的力气。这次轮到他的呼救声淹没在嘈杂之中了。
“好了,我们开始吧。”
她不紧不慢地将范尼克翻过身去,动作粗鲁地扯开他的上衣,用没了热气的塔可塞满了他的口腔,然后将肌松剂直接注射进了他的脊椎里。伴随着一股钻心的凉意直达四肢,范尼克发出了好似蒙在枕头里似的沉闷而又凄厉的尖叫,狼狈的汗水、泪水和鼻涕打湿了他的面庞和衣服,让他看起来还不如下水道的死鱼。
此时此刻,他觉得仿佛有一万只蟑螂沿着脊椎疯狂啃食他的神经,疼痛、酥麻和一种随之而来的无法形容的无力感一点一点吞噬他的理智。当他在恍惚中瞥到艾德琳开始抽取白皇后时,求生的欲望终于击垮了他心中最后的防线,支离破碎的声音透过干涩的喉咙、穿过早已变得湿热粘软的塔可传到她的耳边。
“唔…是我…但我不知道尸体去哪儿了…咳咳…帮派的人…帮派会有人帮我们擦屁股…我真的、咳咳咳咳…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女大学生…你说、说得对…你说得都对…但她不是在痛苦中死去的,是我、是我给了她重生…咳…是我…让她的灵魂自由了。”
范尼克的眼前好像再一次出现那个不久之前的夜晚,衣衫不整的女孩逐渐沉入水底,她的神情平静而又安详,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无上的快感,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宁静。
“那我现在,也给你自由。”
闻言,范尼克的脸色骤变,激烈地反抗道:“不!咳咳咳…我说了、我都说了…我把我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不要,你不能出尔反尔,你不能!”
艾德琳再次举起注射器,“就像你起初选择对站街女下手一样,如果死者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便会无人在意,甚至拍手叫好。你的死亡将会如同一滴雨水落进大海,只有无尽的死寂和黑暗吞噬你。”
“不、不要——!”
一个月后,贝利尔酒店再次出现水质污染,位于东北部的四号水箱中,一具面部朝上漂浮着的男尸被发现。经过三日的封锁,警方以嗑药过量意外溺水身亡结案,整个案件几乎没有掀起任何舆论的水花。
———————————————
*迪迪・布兰查德:【美国吉普赛弑母事件】中对女儿下药的母亲,改编过电影《逃跑》《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