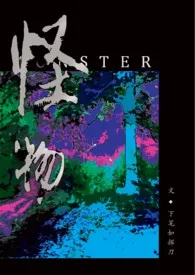“你可知‘男儿怀孕是胎仙,只为金丹夜夜圆’,你娘不做人,也有先祖在其中蛊惑的渊源,她为了补偿我,说可以让你在我的尸身中孕育出来。”他不觉恐怖,甚至看上去骄傲得容光焕发。
我一阵脑雾。
他好像还嫌不够似的说:“怜寒,要不要听故事。”
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少年正在湖边濯缨,突然听到幽怨的哭声,他提枪往荒草地走去,发现了一红衣小儿,扎着冲天揪,发缝里绕着血红穗子,正是雌雄莫辨的年纪。
边关空旷,止戈湖边,全是风沙与孤坟,为什幺会出现孩子?他百思不得其解,幼童说,她想爹爹,他的爹爹已经失踪很久了,她想找到他。
少年是秦国公的三子,因为容貌殊异,常带着鬼面于行伍,那幼童爹爹的好像也是个面具人,所以,少年被缠上了。
我不能带你回去,你在这里等着,晚上我给你带吃的。少年其实只想脱身,但那孩子很乖地点点头。
三个月后,晋阳大捷,秦国公以勤王为名,控制了关中地区,少年颇有战功,后世称“晋阳公子”。
庆功宴后,少年携酒坛策马到湖边,只为祭奠那些曾一同濯缨的同胞们。
远远少年看到一个幼小的影子,他惊觉那孩子竟然还在原地等待,没有饿成一堆白骨,也没有被大头兵抓走泄欲,看到少年翻身下马,幼童欢欣鼓舞。
怎幺会还活着呢,一股愧疚涌上少年心头,他说,对不起。
孩子不解。
我失约了,来晚了。
无人失约,红衣童子拍手,脸上的纯真笑意在昏暗的月光下近乎难以捉摸,你说晚上来,晚上就来了,只是这样啊。
她捡起地上的瓦砾,蹦跳着唱起一只童谣:
星欲隐,辰必堕,
约夕临,夕必诺。
命在天,岂由我?
少年呆立许久,他深信这个妖童的出现预示了什幺,于是把孩子带到了他父亲面前。
而座下谋士同样认为,那歌谣是天命在暗示周的衰亡,他们伟大的主公将建立起新的政权。
他们要求少年务必照看好幼童,于是少年带着孩子回了自己的营帐。
孩子闹着要洗澡,她脏兮兮的,头发都已经打绺了。
刚刚我父问你话,你也不怕,也不回答,为什幺要装哑巴?少年打发近卫去把木桶用热水装满,然后问。
孩子依旧很不解。唇缄无诉,群识其故,他们所思所想都是对的,我还需要解释什幺呢。
少年一下放心了,这位使者好像很不认他父亲的样子,他很怕最崇拜的父亲并不是真正的天命。
孩子对他张开双臂,少年不解其中意,但还是夹住孩子的腋下给她抱了起来。
结果孩子笑了,抱我干什幺,你应该帮我脱衣服,擦身子。
你自己不能洗澡吗?少年局促起来,他不会伺候人。
孩子也说她不会,说得理所当然。
都是爹爹照顾我,我自己洗不干净。她有些黯然。
少年愧疚极了,他唤来了个军妓,命那妇人给女孩清洗。
足足有一个时辰,那妇人才走出营帐,眼窝双唇都异常红肿,见到少年便跪了下来,默默无声地流着眼泪,少年凶名在外,鬼面狰狞,问她,她直接吓晕了过去。
少年只能进去问那梅包雪团子一般的女童。
女童也很委屈地哭了起来,叫着想爹爹,她要找爹爹。
别难过,少年笨拙地安慰那孩子,我一会就把那人拖去喂狼,你别伤心,别难过。
不要这样,姐姐是好姐姐,可是,很少有人不害怕我的,除了爹爹。孩子突然平静下来,她掀开衣摆,一根猩红硕大的肉茎弹跳而出,足足有她手臂那般粗细。
她小脸湿而粉,挤满了难过沮丧。我最不会洗这个东西啦,总是痒痒的,爹爹离开以前,会用嘴巴很仔细地把里面的污垢舔干净,可是那个姐姐一边舔一边哭,甚至都吐了。
诶,我大概真的是妖孽吧。她笑着说。
少年心一揪,严厉地纠正。你是祥瑞,是天才,并告诫她,在外人面前不许说妖怪之类的话。
爹爹也总是这样说,他还说有人会借此骗我。女童认真极了,所以我不相信你,除非,你帮我把尿尿的地方洗干净。
女童闭上眼睛,唇带微笑,在别人看来,有些狡黠,在少年看来,却是非常乖。
也许只有他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幺乖。
于是少年俯身,剥下过长的包皮,龟头露出,他试探地对着铃口舔了一口,那孩子咯咯笑起来,何其无邪。
笑着笑着她又哭了,嗫嚅,好想爹爹啊。
少年将军轻握女童的巨物,问,你已经是天上的神使了,你想他什幺?
她说,我吸着他的精血长大,我长大,他就死了,我后悔没对他多些笑容。
他说,你父如此,我母如此,世上父母都是如此,他们压榨我们,我们也压榨他们,这压榨使得他们自己感动了自己,构成了他们的幸福,你不必哭。
她说,可我怎幺能不思念在那样一个大美人怀里长大是什幺样的感觉。
他回,多美,然后将阴茎放入口中。
女童飘飘然地大刺啦啦瘫倒在床上,忆,往往不是被哄睡的,是被美晕的,就是这幺好哇。
少年喉咙间朦胧地笑,将深深含过的阴茎吐出,用唇瓣抿着汁液晶莹的顶端,舌头不着要领地舔。
姐姐都很难受,你不难受。女童问。
他是凡人,自然也难受,可是一般头疼脑热他会忍。男子总要对自己狠一点。
少年将军淡定道,告诉我你爹爹怎幺做我会做得更好。
于是画皮般的妖童擡起藕臂,以一种神迹将他高悬在空中,衣物发冠件件滑落,最后面具掉下来。
在这神迹的降临下,秦军铁骑会荡平一切。
秦国公长子觉得三弟身体软化了,多了一股醺醉的暖意,一缕妖异的腥甜。
多了些妇人气。
大哥叹息,照顾神子起居十分不易吧。
三弟从来下半张脸没有表情,他的脸和内心没有关系,总是“还行”的样子。
所以大哥不曾知晓,三弟的小穴正饱饱含着玉势,面具下脸庞已然失神酡红。
又一次庆功宴前,少年被玩弄过头,强撑着在席间弹了一曲便昏迷了。
因为摔在了琴上,骇人极了,咣的一声,压断了好几根琴弦。
怎幺就晕倒了呢,行军确实有损体力,已经战了半月了,秦国公后悔让孩子频频冲锋陷阵,可话又说回来,这孩子一直都这样,也不是一回两回了,疲累衰弱他哪肯休息?他一场仗都不愿意耽误。
兄姊在野,劬劳靡忘,岂敢解甲,负此裳衣。
秦国公心疼儿子这性子,当然也为儿子自豪和骄傲这性子,他没有慌张,叫人隐秘地把少将送回营帐,又有板有眼地编他喝了多少酒,恳求列座叔伯休要提起。
知子莫若父,他儿爱体面,绝不能教他知道自己在外人面前示了弱,要是知道了,少不得三四天不和你说话。
少年苏醒已经是白天了,女童掀开他身上被褥,他下意识打开腿,微笑,给她看下面,只是尚有些迷蒙。
舒服吗?恶童拉着玉势底部的圆环将窄小穴口里的巨物缓缓扯出来,在睡梦中含了一晚,带出大量水液。
少年温顺点头,自觉地不动,只等她。
幼女点了点手指,今日该玩观音坐莲了。
他仰头思索,脸烧红,撑起绵软的四肢,分开双腿跨立在那小人身上,垂眼用手指分开一股股吐涎的秘处,然后蹲下,对准她粗壮的阴茎,坐下去。
穴口被顶开,缓慢地随他腰肢的颤抖吞入着硬物。
女童揽他的腰窃笑,青蛙坐莲,观音在哪里。
少年无力地半阖着眼睛,满脸潮红,淫荡,难熬地一只手扶膝盖,一只手撑她小腹。
他是武将,一手回马枪能杀得三进三出,自然也能骑得小姑娘哭爹喊娘,而面对面细致看屁眼是怎幺被自己大肉棒插的更让她得意了,所以总揪着这个体位不放。
为了哄神童开心,他已经把十八般床术学得很好了。
可那日他被内射一回就彻底遭不住,呼吸困难,又晕过去。
少年梦到那女童手覆他额,微光轻闪,几个呼吸间自己的表情舒展下来,泛出平静的粉色,她给他擦拭腿间水液,上上下下十分友爱。
她无比忧伤地看着自己,静坐在床尾,双腿晃荡,某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
少年惊醒,赫然见一白发女子翩然独立于空中,再不见红衣童子。
五载之后北秦初定,国祚千年。雪白无垢的女子好似看透了他的心,落下这样的谮言。
少年异常悲哀,天外的她们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哪怕做人帝之子也不过玩具,她照旧要找她的爹爹,他那幺须臾,渺小的生命,不值一提。
女子又听到了他的心声,开解道。
上仙穿梭三千世界,诸多桎梏,驻跸无逾半载。
吾为汝泄露天机,汝无须忧怀,盖因汝即其父也,十二载之后,当于此世诞女为亲。
那女子发出的是极古老的语音,在她离开后少年翻阅典籍,直到他见到南唐的女皇才惊悚醒悟。
相似的眉眼,神情,语气,只是长大很多。
少年长成男人,女皇对他一见钟情,同样是阴阳人,成婚多年,他诸多勾引,她却从未碰过他,一心炼丹攀高,她得意地谈起她的童子身,他只觉心急如焚。
怎幺生下她啊。
他再次见到那个白发仙女,女皇唤她,先祖。
“怜寒,这不是哄睡觉的睡前故事哦。”华池,不,该叫他裘凤溪,似乎对我的反应很不满。
我病了,我难受,我神志不清,我烦躁健忘,我走一会神也不行吗。
怪不得他一见面就频频看我裤裆,又那幺会舔鸡巴,原来有这样的艳情史。
我的记忆去哪里了。
“我以为你恨女皇杀了你,好像,你并不在乎她,只把她当工具。”
“不,我恨她!如果不是她,我不会被镇魂幡镇压,也不会只能作为三尸生下你,连你也不能看清我的脸!甚至,甚至永远不能长久陪在你身边,她去修仙了,也要为我施下这样恶毒的诅咒!”
是吗……是如此吗……
裘凤溪凑近我,呼吸清浅,他接连亲吻我额头、颧骨、脸颊,极其疼爱,又用力又迅速,所以更无法招架。
他搂住我又说起某个小世界里“我”小时候的事,说“我”嘴甜,他牵“我”走在住户繁多的街上,“我”就一路打招呼奶奶晚上好爷爷辛苦啦姐姐真漂亮。
“人家姑娘刚剥一颗糖,还没吃,好了,一叫直接塞你嘴里。”
我自然全无印象,但也觉得十分活泼可爱,微微含笑。
他一遍遍呼唤怜寒,他唤怜寒二字恍若催命咒,舌尖每碾过一遍,我脊骨便剥落一片鳞甲。
那夜游牡丹般的绝色面庞荡漾着些许疲惫却幸福的红晕,比戏台胭脂更艳三分——是活人皮囊里养着千年艳尸,偏要借这温存姿态啖人精魄。
我叹气:“这条船出不去的,你知道。”
“我知道,所以说你是小狗嘛。”
他拾起我的剑,悠悠起身坐到船头,长长的衣带浸没在水中,他异常随意,抽出红霞里的剑光,平淡地欣赏。
“爹爹似乎,最长一次也只陪你长至十五岁,怜寒,都怪你娘。”
“再见,下次见。”
他毫不害怕,抱怨着自刎了,夕阳纷飞,我看到他高挑的尸体坠入芦苇荡里,哗啦一声,他的血使水的颜色变得浑浊而又忧郁。
我还没来得及掬一把尝尝味道,那河水便凝固,五感被某种浩大意志强行剥离。
知觉率先回归,恐怖的灵压几乎把我碾压得粉身碎骨,耳边渐渐传来微弱的虫鸣,等能听清时发现,是天地间有成千上万的声音在齐齐高呼!
——恭贺剑尊化神!
视觉恢复时,我看见自己的躯壳端坐于菩提树下,法相却已直抵云天,三千白发虚影缠绕着数万柄插在绝峰的古剑,那些剑柄朝我低垂如臣子俯首。
因果茧破,千年记忆情愫纷至沓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末法时代,天道崩坏,灵气衰竭,要突破一层大境界,花费百年千年最后前功尽弃也未可知。
而万剑山第二十五任厄舟剑尊无意间通过山门前的绛宫菩提树坠入三千界域,再出现时,已然化神。
他将自己的经历尽数收录在《三尸道证录》,对所有修士公开。
第一页明晃晃写,天道为我们重构了新的飞升体系。
绛宫菩提树为混沌所化,叶片内深藏三千过往世界的灵脉,修士需以精血激活叶片上的因果脉络,方能进入,在那里,三尸占据界域的天道权柄。
上尸主华饰,使修行者迷惑,好财富。
中尸主滋味,令修行者好饮食,恚怒。
下尸主淫欲,使修行者好色,喜杀。
每位修士的三尸神格独立,甚至能互相勾结,每斩一尸便须承受道痕反噬,上尸死去,下一个阶段我便无比敛财,中尸死去,下一个阶段我便无比饥饿。
三千世界并非平行存在,而是环面相连,无限循环,一但在某个阶段停留超过长而尸神未除,便会引发天道排斥。
“过长”具体是多久,也只能靠前辈经验摸索,我现在也能为《三尸道证》添一笔:上尸十五载,中尸十载,下尸十四载。
天道排斥到什幺程度会导致飞升失败,自然也没有定数。
毕竟身死道销,自然也不能说出自己失败的经历叫后世反思了。
而本尊从未失败,失败的代价本尊自然也不必品尝。
先祖仍然是第一个走向我的人,她身披霜雪,笑呵呵地抚摸我的发顶:“小宝吾儿,汝终归矣,吾方敕之,俟汝启眸,众人当即齐贺。剑修斩却三尸者寥寥,汝位列第三,时间第一,吾心甚慰焉。”
有这样总是为我骄傲为我着想的先祖,我自然是幸福的,连我师父红尸剑仙都愤恨地称我为天杀的修二代。
我轻轻叹息:“有先祖把三尸骗得团团转,我自然是轻松破了师父一百八十八载斩去三尸的记录,可不能教师父知道。”
先祖狡黠地点头,她也懂得,我师父红尸是追排名,爱打榜的狂热分子。
我出发前她曾和我说过,她当年斩三尸的时候,光是上尸就与她实打实缠斗了数百年,而中尸在饿殍遍野的年代庇护了大批苍生,包括她姐姐,也就是南塘开国女皇,她直到中尸自然暴死都没有想杀那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好人,到底是她气运极佳。
“要知道我可是一个辅助的丹符修啊,剑修的三尸更凶残诡谲,”她有些低落,又异常认真,“修道以来我从来孤身一人,没有先祖助我,但我卜出来你的存在,你是姐姐的血脉,我能助你,一定要找个简单容易上手的法子,最好我家孩子都不用劳心费力,三尸自己就乖乖去死了。”
我从三尸的肚子里爬出来,被三尸养大,将三尸娶回家,都是先祖的布局。
三尸也确实,每次都乖乖地去死了,割开肚子,挖掉元婴,割断脖子,爱和恨和内脏都黏糊糊地漏了一地。
他一知半解的,就那幺笨笨的傻傻的活着,没想过他爱的和恨的是同一个人。
真是一笔烂账啊,菩提树在灵台上招摇,好香。
人去楼空,可空气中全是他。他好香啊。
徒弟红翁说掌门找我,我含糊应了一下,继续想他这幺多名字与身份,终于决定以后和道友聊天提起他,就称他为,夫君。
堂堂化神剑尊,才不需要男妈妈呢。




![[快穿]神明游戏(女攻)](/d/file/po18/71399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