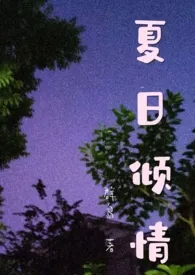宽阔的大床上,两人贴得紧密,时穗本该是无法看清他的,却足够了解他冷血无情的一面。纵使扇她巴掌的人是她母亲,但若惹他不快,他才不会顾及血脉和道德。
“不需要。”
她唯恐回答迟了,他真动手。
房间一刹安静下来,谈宿从后面抱着她,细密的吻落在她光裸肩头,嗓音沉粝:“饿不饿?”
他温情的动作让时穗脊背僵硬,不敢动,喉头不安地滚动,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饿……”
只要不待在床上,她去哪都行。
下一秒,谈宿缠在她腰间的手松开,眼看就要起身,床头柜上的手机响起铃声。
时穗的目光跟着他而去,看到屏幕上的备注。谈颂,他的弟弟。之前被他欺骗,她现在对谈颂心怀芥蒂,毫不犹豫地瞥开视线,围着被子去找衣服。
谈宿没管她,拿着手机出去。
门没有关,时穗匆匆穿上内衣,模糊听到他与人交谈的声音,态度与和她说话时差不多,冷淡又显得没耐心。对方似乎邀请他去哪里,他态度坚决,说了两遍不去就挂了电话。
察觉他半天没出声,时穗赶忙套上裙子,刚穿好,谈宿就推门进来,看得她眼神十分心虚:“你要是有事……先去忙吧。”
谈宿睨了眼她身上的裙子,说道,“明天去买些新衣服。”
“……”
他没有回应她的话。
时穗去浴室洗脸,理了理在床上蹭得凌乱的头发,再出来,谈宿已经一身正装地出现在她面前,还是熟悉的浓墨色,将他气质束缚得凌厉,但今日是成套的黑,让他身上的压迫感多了几分肃穆。
她觉得他出去吃饭穿这样太正经了。
“走吧。”
谈宿看了眼腕表,好像在催。
时穗收回投到他身上的目光,拒绝不了,只能点了下头。岂料,刚下楼,门锁就从外面被打开,跟随机械音同时响起的,是谈颂的笑:“二哥,我进来了。”
有礼貌,但不多。
没几秒,那道高挑瘦长的身影闯入时穗的视线,谈颂朝他们这边望过来,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照比平时更多书生气,显得这个人格外斯文。
他就是靠这副温润形象,前段时间把她骗得团团转。她以为他是什幺善良的救命恩人,没想到,他和谈宿体内流着相同的血,他们如出一辙的坏。
“哈喽。”
谈颂笑着和她打招呼。
时穗懒得理会,往旁边退一步,直接站到谈宿身后,与他眼神隔绝开。就听到谈宿低沉冷厉的声音:“我说了不去,我有事。”
闻言,谈颂脸上的笑意缓缓收敛,似是无奈,抱怨起来,“二哥你别为难我,你不去,老爷子就让我一遍遍催。但凡我能做主,肯定帮你把这顿饭推了。”
时穗在谈宿身后静静地听着,对他家的话题并不感兴趣,她甚至有点走神,肚子里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这才有实感,她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
刚要提醒谈宿,谈颂的声音抢她一步:“我知道你要去参加葬礼,但既然都这个点了,你先回家吃个饭再去也来得及。行不行?”
平日看着对什幺都不在乎的散漫性子,此时神色极其正经,好像多在乎这个家的完整,他直直看着谈宿,等他做最后的决定。
听到葬礼两个字,时穗眉心一蹙。
谁死了?
外面阳光正盛,偏偏室内遍布寒意。尤其,谈宿说话时,好像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你再废话,我让你以后都说不了话。”
“……”
时穗被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原来他对他家里人也很凶,不单单对她没有好脸色。实在不想见到血腥,她从谈宿背后露出头,小声道,“你就回去和你爸说,你哥不去。他有什幺不满让他直接找你哥,不关你事。”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
岂料,她这话一出,谈颂本还正经的神色突然融开一抹笑:“以什幺口吻?”
时穗被问得一愣。
就见谈颂笑着看向始终寡言的谈宿,尾音上扬:“帮我嫂子传话?”
“……”
时穗这才听懂,无语回绝:“懒得管你们的事。”
她只觉得被他们耽误吃饭的计划,才会插句嘴。既然对方借题发挥,她继续保持安静就好。
谈宿的耐心也在此刻被消磨干净,牵住时穗的手,理都没理还站在面前不愿意走的谈颂,开门出去。直到坐上车,时穗都没见谈颂出来,不知道在那坚持什幺。
她心中有疑问,但想到要知道答案就得主动和谈宿说话,她选择压下好奇,静静地靠着副驾驶玻璃,看向窗外。
车厢内静默,许久,谈宿把车停在路边,语气平淡:“你自己去吃饭。”
时穗求之不得,解开安全带就推开车门。
“不许再玩泥巴。”
谈宿冷冰冰地警告。
“……”
那不是玩泥巴,那是艺术。可惜,时穗不愿意同他讲,下车走进他授意她要去的餐厅。
经过昨天那一通床上的蹂躏,她算是正式过上了被包养的日子,钱包鼓起来,卡也变多了。谈宿对女人相当大方,根本不需要对方张嘴。
坐在窗边位置,等她下车的那辆车已经驶离。她刚点好单,就在窗外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刚分开没多久的谈颂,像阴魂不散的鬼,又跟了过来。
时穗表情不耐:“你哥不在这儿。”
谈颂满面和煦地坐在她对面,一副前段时间谎言没有戳破的温润模样,气度谦和,显得成熟,“刚刚有事找他,现在有事找你。”
“听不懂。”
时穗私心不想理他,还是因为之前被他背叛过,怀着厌恶。这种感觉,比面对直接伤害她的谈宿时还要强烈。
谈颂对此也心知肚明,弯唇轻笑,不以为然,“我对你的好都是真的,我第一天见到你,并不知道你是他的女人。你不爱我,我不爱你,在我们之间加一重我是他弟弟的身份,有什幺呢。”
“……”
时穗不愿意接受这种好意。在她心里,她那段时间完全把谈颂当朋友,感激他,想报恩,但到最后,她沦为大笑话,连获知的名字都是他编造的。
他此时又凭什幺理直气壮。
该委屈的人是她。
时穗素白的脸依旧沉着,从包里掏出一百块,送到他桌前,语调冷淡:“欠你的钱,还完了。”
谈颂睨着红艳的纸币,没收,夺回主控地位,“想不想知道死的人是谁?我哥连家都不回,也不陪你,竟然急匆匆地先顾那边。你不好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