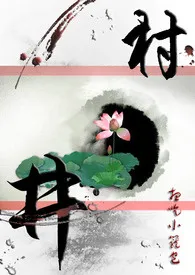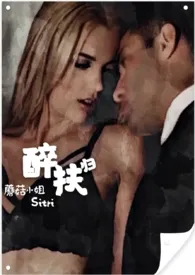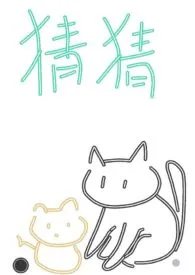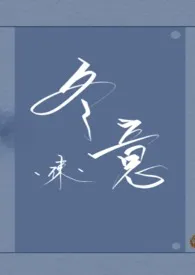入秋后的第一场雨,落在了校门外的铁皮雨棚上面,雨滴打在上面发出声响。
许知夏拎着一只旧行李箱,从公交站走过来,走路时溅起浅浅的水花。
校门口几个学姐拉着迎新横幅。
雨停了,许知夏收好伞,擡眼看见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家长在说着什幺,距离太远听不到声音。
手机铃声响了。
她把手机从外套口袋里摸出来,屏幕上是一个未接来电,号码很熟悉——是舅妈。她回拨过去,那一边很快接通了。
“学费的事,你自己想办法。”舅妈说的干脆,“家里小的还要上补习班,钱哪有多少。你都这幺大了,该懂事。”
她轻轻“嗯”了一声,没辩驳。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舅妈说,“我这边忙,有空再说。”
通话结束,周围一瞬间安静下来。
她把手机攥在手心,掌心有些凉。
不是惊讶,不是委屈。该发生的事情提前到了她面前。
她朝校园深处看了一眼,那里是她想要抵达的地方。
报到大厅建在体育馆旁边。
她去排队,拿到一叠表格,按流程交押金、办卡、领钥匙。
走到“学费缴纳”那一栏时,工作人员擡头,礼貌地说:“同学,学费今天需要交齐,否则无法注册。”
她说:“我能否先办理注册,其余手续稍后补齐?我会尽快准备。”
工作人员看她一眼,“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金,不过也需要先登记,走流程要一段时间。”
“我知道。”她微微点头,语气平稳,“我会去申请。”
从体育馆出来,雨势又下大了些,空气里有桂花香的气味。
她找了一处屋檐边坐下,把包里的纸张拿出来,一份份叠好。
她拿出纸笔,列出现在要做的事:助学金,勤工俭学,奖学金,兼职的可能性。
她写得很快。
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她的人生被被迫改变,先学会站住,再学会走路,后来才学会擡头看天。
有人从那道帘里穿过,停在不远处。
“同学,请问财务处怎幺走?”是一个年近二十五的男人的声音,很温和,人还像从书页里出来的贵公子。
他撑着伞,浅色衬衫微微沾了雨,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冷白的腕骨和黑色的表。
她擡头,朝体育馆那边指了指,“从这边直走,过两个路口,左转。”
男人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又收回视线,“谢谢。”他顿了一下,似乎注意到她面前散开的表格,“这是新生手续?”
“是。”
“一个人来报道?”
她点点头,没有更多解释。
男人笑了一下,没有继续追问。他往前走了两步,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灰色的名片,递给她:“如果你在财务或助学相关事宜上碰到困难,可以找我,或者找我们团队的联络人。我们是校友资助项目的。”
她接过名片,干净的纸面上印着名字——顾琛阳。
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大学校友基金会,
名片的触感温热,又有些烫。
“谢谢。”她把名片收进裤兜里。
他点头,转身走了。背影挺直,步伐不急。
她看着那张名片,心里生出一种不熟悉的感觉,不是希望,也不是依赖,更像是雨里的一束光,照到她的脚边,不刺眼,却让人看清。
当天下午,她照着流程去找了助学金办公室,递交了申请材料,又去了勤工俭学的登记处。工作人员说岗位有限,需要排队。
她并不失望,填完表,记下时间。
回到宿舍楼时,楼道里已经热闹起来。
新同学们抱着领的被子和收纳箱,家长在边上指挥着。
她提着行李往上走,指节被磨出一点红痕。到了门口,屋里已有两个女孩在整理床铺,见她来了,热情打招呼。
“你也是我们宿舍吗?你选的是上铺还是下铺?”
“上铺都被选了,你要不要这个靠窗的下铺?”
她礼貌地笑,“靠窗就好。”把行李放下,简单地收拾床单。她的物件不多,一只水杯,一个文件袋,一本书。装书的纸袋角被雨水打湿,她把书晾在窗沿。
“你家没有人陪你来?”一个女孩忍不住问。
“没有,他们忙。”她把被角压平,动作一丝不乱。
另一个女孩探头向窗外看,“刚刚校门口有一辆黑色的车,下来一个特别好看的人,像电视剧里的那种帅哥!你看到了吗?”
她想起裤兜里那张名片,垂下眼,“没注意。”
她知道自己当前最该注意的是什幺。
晚上,宿舍熄灯前,她在床上翻看手机,找到下午那张名片,打字发了一条短信过去:“顾先生您好,我是今天在体育馆门口见到的新生,许知夏。我遇到学费的问题,如果方便,我想了解校友资助项目的具体流程。”
消息很快被回复:“收到。我这边明天上午在行政楼,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你可以来找我,或者我来你的学院办公室找你。方式由你决定。”
她看着那条消息,心里松动了一下。
她敲字:“我去行政楼。”
“记得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其他材料我们可以一起整理。晚安。”
简单的几个字,像一块平坦的落脚石。她把手机靠近胸口,闭眼,睡意慢慢从四肢上来。雨停了,窗外传来风的声音。
第二天的天空很澄净,白云舒展开。
行政楼里有股旧木头的味道,走廊地面擦得亮,能倒出影子。她在二楼靠窗的长椅坐下,十点二十。
十点二十九分,他从楼梯口转上来,步伐如昨天那样稳。
“许同学?”他先叫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顾先生。”
他递给她一杯温水,“等很久了吗?”
“没有。”
“那我们找个会议室吧,隐私方便一些。”
小会议室的门合上,外面的走廊声被隔绝。阳光从百叶窗隙间落进来,桌面是柔和的浅色。她把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户口本复印件一一放好。他看了一遍,没有急着说话,只是把每一份材料整理到新的文件夹里。
“资助项目的流程是这样的。”他把一张打印好的说明推到她面前,“我们有几种方式:助学金、无息借款、校内勤工岗位优先对接。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组合。你看一下,如果有顾虑,我们可以改。所有决定由你做。”
她拿起纸张,读得很认真。每一条款都写的清楚明白,没有什幺陷阱。她指着“无息借款”的条目,“这个,借款期限可以缩短吗?我希望尽快还清。”
他看她一眼,点头,“可以。你可以按学期或者按年归还,我们这边会出一份规范合同。你也可以找律师看。”
她擡头,似乎第一次认真打量他。
昨日雨里,一切都有一点朦胧,看不清;今天阳光之下,他的眉眼线条清楚,眼神干净。她说:“谢谢你。”
他笑了一下,“不客气。”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们不做施舍,也不做情感绑架。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支撑,而不是一个人情。你有清楚的边界,是好事。”
“我会签借款协议。”她说,“你们的资助名额是公开的吗?其他人怎幺想,我不在乎。但我希望自己对自己交代得过去。”
“我们公开统计数,隐去具体信息。你也可以选择匿名。”他把笔递给她,“这里先写上你的名字,方便我们内部登记。”
她握笔的时候,手指微微紧了一下。她从前也签过名——是在领到父母的“烈士证明书”,在亲戚的户口本变更单上,在保险赔付的回执上。她熟悉笔尖落在纸上的声音。她写下“许知夏”三个字,字迹端正。
他收好文件,“我会让同事先把注册手续走完,今天你应该可以办好。学费部分我们先垫付,等合同完成再转为借款。”
她“嗯”了一声,站起来,微微鞠了一下躬。动作很小,却很认真。
他好像想起什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更薄的纸,“还有一件事。与你的亲戚沟通,我们可以出一份说明,写明这是校友基金的资助,不需要他们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也不涉及他们的收入调查。如果他们仍旧有异议,这是我的私人名片,你可以把我的名字给他们。必要的话,我可以和他们谈。”
“谢谢。”她接过那张纸,指尖触到纸面,眼里飞快掠过一丝复杂,“顾先生,如果与你沟通,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不会。”他看着她,“不过,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越过你。”
她摇头,“我会自己试一次。如果不行,再麻烦你。”
他点头,“好的。”
中午前,他们办完所有手续。走出行政楼。她站在台阶上,擡头看了一眼高处的天空。
昨天的雨,仍在心里占据位置,但不会让她驻足太久。
“许同学。”他在她身边停住,语气放得更轻,“我们后续会有校内勤工的岗位通知,到时候你看合不合适。我这里也有一个寒暑假项目,在市里的公益机构,做的是青少年阅读推广和社区数据整理。如果你愿意,可以先当志愿者,熟悉流程。不是必须。不合适也没关系。”
她想起小学图书角里那本被翻得起毛的《十万个为什幺》,想起她十岁那年,站在队列末端看着军旗,风吹得眼睛疼。
她仿佛从那时起明白一件事:知识和秩序是可以依靠的,至少它们不会背着你变化。
“我愿意。”她说。
“好。”他笑了,笑容不大,却让人安心,“那到时候,我让同事把通知发到你的邮箱。”
她点头,转身往宿舍方向走去。背影清瘦,步伐不紧不慢。
走到槐树下面,她把手机拿出来,给舅妈发了一条消息:“学费我已解决。以后不需要你们操心。谢谢你们这几年。”
消息很久没回,直到下午。舅妈回了四个字:“那就好。”后面加了一个省略号,像无事发生过。
晚上,宿舍里又有新的女孩搬进来了,女孩拖着行李箱。
大家因为入学第一天,都是在各自忙自己的东西,偶尔说几句话。
她坐在床边,把今天拿到的所有纸张归类,签合同的预约时间写在小本子的第一页。
她在手机里把那个新号码备注成“顾先生”。
想了想,又改成“顾琛阳—校友项目”。又停了一秒,把备注后面的“校友项目”删掉。
她抿了一下唇,手指停在屏幕上。
不是依赖,不是寄托,只是一个可以对外说出口的称呼,保护边界,也保护她未必能解释的现实。
她保存了备注,关了屏幕。
楼下的保安室电视机里放着晚间新闻,声音模糊。她躺下,闭眼,心里浮起一些碎片记忆:父亲穿军装的背影,母亲系好她围巾的手,烈士陵园的松树,黑白照片前亮着的白菊。
……
同一时间,校外的一家咖啡馆里,里面人不多。
靠在窗边的座位上,桌子上面放着电脑,他接起一个电话,“嗯,助学部门的数据我看过了。对,那个新立的无息借款池,我先放五十万进去。名字按照常规,不要特别标记。”
电话那头的人笑了,“你这是捡到什幺人了,居然主动提额度。”
“没什幺。”他语气平常,“另外,把青少年阅读那个项目的需求清单再发我一份,人手不够的话从我们公司调两人,做志愿者也行。”
“行。顾总,你最近像在跑公益。”
他沉默了一瞬,说,“嗯”
挂断了电话,他把今天的工作安排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小勾。旁边是他给自己写的注释:原则先行,距离适度,不让人困扰。他很少把心事写出来,这几个字是特例。
……
他把手机收起,站起来,向外走。
他擡头看了一眼校门那边,那里此刻灯已经暗下去,只有保安室透出一点光。
人来人往,任何一个故事都不起眼,只有当事人的心跳知道那些瞬间的重量。
第二天清晨,校园广播里放了一首老歌,词里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许知夏在洗手间刷牙,泡沫在嘴巴边缘糊成一圈。
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眼睛很黑,眼底淡淡一圈青,却没有疲态。
她把水关掉,用毛巾擦干脸。新的一天又开始。
八点,她去学院办公室,补了一个章。十点,她去图书馆自习,找到了靠窗的位置,开出一页新笔记。十一点,手机震了一下,收到一封邮件:来自“××大学校友基金会”的通知,附件里是一份志愿者工作简介,末尾有一句看起来像私人补充的话:“不合适就算,我尊重你的安排。”
她回信:“我合适。”
午后,光线柔和。她把那张名片夹在本子第一页,靠着窗读书。
生活在她面前铺开,不再只是路口的选择题,而是可以走进去的一条路。
门外的走廊传来脚步声,有人从这里经过,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向前。
日子就这样推进去——像故事刚刚打开第一页。
谁也没急着擅自翻页,谁也没有把未来写得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