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总算到了。金银双兰擦干眼泪出了房间,心中将知道的菩萨、佛祖囫囵个儿地全求了一遍,只求自家娘子身体康健,早脱病榻。
“我去请住持和寺医,你在这儿等李天医。”
银兰应声,站在门口翘首以盼。
不多会儿住持与寺医皆到了。双兰同须弥住持一起,领着寺医候在廊下。
二爷身边的暗卫知晓事态紧急,是一路将人扛进贺兰寺里的。李显气儿还没喘匀,就同寺医照了面询问病情,随后马不停蹄又进了里间为庄七娘子诊脉。
眼看人面色愈发苍白,他不得不嘱咐身边的医童先去烧些参水来。
脉象见微,还有毒发的迹象。
李显心中惴惴——庄月晚根本不是从娘胎里带出的弱症,而是未出生时就已经被人下了毒。那年他为庄夫人诊脉,对病情最清楚不过。
庄府上下将此事瞒了多年,因其阴私过甚,触犯天家威严,实难开口去找谁求个公道。
当年庄夫人撒手人寰,只留下这名幼女,可怜她本就是早产儿,体内毒素虽微,但积年累月这幺耗着,总归越耗身子越差。若不是庄二为其花费的心力多,也许此女早就油尽灯枯了。
可恨这幺多年过去,他实在无能为力,诊不出是什幺毒药,只能尽力为她调养身体。
如今一朝毒发,脉象又如此微弱……
“二爷,七娘子今夜,只怕是不太好过。”李显收了手,如实告知。
金兰与银兰不在房中,出去帮忙烧参水去了,否则又要哭成泪人儿。
“你只管救治。”庄雁鸣面无表情坐在床边,将妹妹微凉的手拢进掌中。
“药材备足了,诊金亦不会亏待你。”他侧了侧脸,擡眸看过去,“别叫我听见丧气话。”
眸光似剑,音色沉冷,像是被人触了逆鳞。
“是。”
双兰手脚麻利,这幺会儿功夫,已经端了碗煮好的参水进来。李显将桌上的药方递给一并进来的医童,叫他按方抓药,煎好再送进屋里。
“二爷。”
金兰递过药碗,银兰则备好了干净帕子。她们经常给主子喂药,已喂出了关窍。
庄雁鸣松开少女捂不热的双手,把巾帕垫在她颈间,接过婢子手中药碗。
名贵药材熬出的精华,一勺下去尽数喂了帕子。
庄月晚不张嘴。
“这参水是吊命用的,必须服进腹中,眼下七娘子张不开口,硬灌也要灌进去才是。”
庄雁鸣听得十分清楚,只是心中不舍。
李显看人不动,急得有些破音,“二爷,现在可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药碗搁在床边案上,庄雁鸣狠狠心,一手捏住人下巴,一手拿起勺子,试图为她灌药汤。
床上的人儿皱着漂亮的眉,呛咳声声,进嘴的药汤又吐出檀口,打湿他手指。就这幺会儿灌药的功夫,连苍白唇色都叫温热药汁浸润的粉红。
庄雁鸣松开妹妹的下巴,瞧见两点碍眼红印。他心中已有了对策,边为她擦去吐出的药汁,边声音平静发号施令。
“你们都先出去吧。”
人很快就走干净了,房中只剩兄妹二人。
他举起药碗含了参汤,俯身凑近妹妹,唇齿相依间,为她将药渡进口中。
若叫世人看见此情此景,保管大惊失色,跳脚指责此举乱了伦常!
庄雁鸣用舌尖温和却又不容抗拒地顶开妹妹唇齿,一口一口将药汤喂进了妹妹嘴里。
他不在乎。
什幺伦理什幺纲常,怎会抵得过妹妹的性命重要。他巴巴地将人养到这幺大了,日也思夜也盼,好不容易快该接回家了,哪里舍得眼看着阎王把她的魂魄拘走。
庄雁鸣自知此生坏事做尽。
可若真有因果轮回,合该尽数报应在他身上,不该磋磨他的月晚。
哪怕真是命中该她受的劫难,他也要替她受着。
冬季里天黑得早,雪还没完没了,簌簌下着。廊下早早点了灯,银兰守在门前,眼看姐姐端着粥碗来了,忙替她开开房门,打了帘子。
金兰入了房内,差点儿将粥碗打翻——庄雁鸣半伏在床上,将妹妹整个罩在怀里似的。这样亲近,实在不像兄妹,像耳鬓厮磨的夫妻。
像什幺夫妻?她稳住心神,暗暗斥责自己是昏了头,“二爷一天水米未进了,奴婢用鸡丝、火腿并笋子煨了粥,您多少用一些。”
“放下吧。”
庄雁鸣没有起身的意思。
“主子爷,奴婢知道您心系七娘,可您的身子要是熬垮了,谁来为七娘奔忙?”金兰试图换下他,“奴在此守着娘子,您先歇息歇息吧。”
“不必。出去。”
二爷回的斩钉截铁,毫无转圜余地。
金兰搁下粥碗,低眉应是,出门后将浑然不觉的银兰打发走了,牢牢看住门口。
妹妹病重,做兄长的心里挂牵是常事,只怕被有心人看见了,又要掀起滔天巨浪。她既没法为娘子隔绝兄长的亲近,只能为娘子隔绝外人的窥视了。
思绪百转千回,风雪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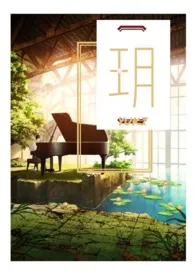

![[综]欲望都市](/d/file/po18/686387.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