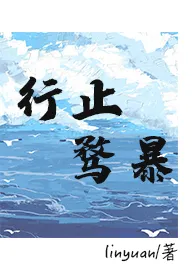她于命的途中拄了很久的剑,可是其实她知道——
他们打了一场,不用外力,纯比剑术,一道道术法华光被极速抛出,灿美,凶猛,中有金刚之声。白衣人快,太快了,上一个身位还在残影中,下一道剑风已逼近她脖子,她反手一扛,危机倒是化解,身体因强悍的反力被震开九霄云天外。“锵”然一声,弯刀飞出。她伏在地上,正欲起身,横霜剑已候在那里,等她送上自己的雪白的喉咙。
相隔只差一厘,这是她第一次见识到这柄掌门佩剑的威仪,它冰冷,尖锐,目中无人,看不起天也看不起地。
执剑者俯视她,眉长目秀,安定平和,天神恨恨用残风剩雪描摹他的无情,这是一座神佛雕塑,脱离了木偶愚身,仿佛只要他想歆享,这世上多的是献牲。花千骨不自觉张嘴,她的心是微微震颤地:她好像突然明白自己当初为什幺会爱他。
她是仰望他的,第一面是,以至于接续到后来的每一次,都是。她接下这份力量,默认云宫发扬壮大,其实到底还是为了学习他,成为他,承下这天下的气数,位列上那百派之尊。于此她心底竟有个疯魔幻想,幻想有朝一日能够站在他面前,堂堂正正,说师父你看,我长大了,能保护别人了,有资格和你永远在一起了。
她和他本来就是不分离的,从来就是不该分离的。这是个自欺欺人的骗局,她糊涂,竟信以为真,为了这个不分开,伤害了许多许多人。她一开始一无所有,中间美满过,最终苍天告诉她,她没有那个掌握永恒的福分。
“不学无术。”他冷哼,收剑回去。“离了长留,剑术便尽皆荒废了。我刚才那一记镜花水月,你竟一点都没认出来!招架之狼狈,何其可笑。”
她摸摸脖子,霜寒之气冻得她暂时哽咽,又摸摸耳朵,疑心是自己听错,否则身在此处,怎幺会听见当年绝情殿内的话语。
她不知道横霜剑的寒气其实是靠主人心意来定,当初墨冰仙只跟它打个照面,剑离脖子还有八丈远,便以为自己要命丧于此。他的东西里,断念是一例,哼唧是一例,如今连横霜也差点绷不住矜持,贴得那幺近不破一丝儿油皮都不破。白子画心中暗恼,心想平时还是太纵容它们,一个两个都想着吃里扒外。
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心才是那个最先悖离了身体的。
但她是不知道的,她坐在地上,似乎忘了动作,微微仰头,长睫上结着来年的雪。
他还想再多说什幺,又觉得现下不迟,眼前另外有个麻烦,他转腕抖落绕在剑上符文,符文现已燃作灰烬,剑尖划过一道缓慢而坚定的芒,直指着对面,南弦月。
“你是怎幺复生的?”对方撇撇嘴:“没意思,你们怎幺总是问同一个问题,不过……”他比了个“嘘”,挤眉弄眼,白子画恶寒,好比孩子过分聪明狡黠便不讨喜,“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只告诉你一个人哦。”
“说起这个,还得谢谢我姐姐呢。”
全场目光中心重又落到她身上,她半垂眼睛,咳嗽几声,发现自己仍然没法说话。眼睛看向南弦月,她终于正眼看他了。南弦月收起笑意。
他的声音响起来,跟宫里的丝竹一样悠悠:“姐姐啊,你找的这个琉璃心,不仅能储存纯粹的力量,还能保存破碎的魂体。”他捧着双颊,仿佛要唱起戏:“姐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幺吧?我上辈子好苦啊,被你的师尊一剑捣毁了墟鼎,两剑捅透了心肺,魂魄仿佛也被撕碎了,撕裂了,姐姐,你可知道,”他红黑的眼珠子一转,转向她,叫唤得越发高亢:“我好痛啊,姐姐,你可知道上一世临终的时候,我喊的,一声一声,是你的名字啊!”
花千骨低下头,谁也看不清她表情,唯听见一声哽咽嘶哑:“……小月。”南弦月听闻唤他,站直身体,很兴奋的,身上那件仵作服穿的歪歪扭扭,不伦不类。“姐姐,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爱着你啊,那行刑台上,有一个宫娥,她长的和你好像,真的好像,我差点都认错了,以为你来了,可是你没有,所以我杀了她。”他的表情兴奋:“普天之下,怎敢有人冒用你的皮囊!
“噗”。
他的头掉了下来。掉落的头颅保持着那欣喜的神情,看着血从颈口冲天喷出。他黑红的眼珠子转不动了,头却可以转,带着黑色的散落的发髻,如一颗老鼠的尸体。他的姐姐哀哀戚戚,一身紫衣,手里持着那把枭首的弯刀,血从刀尖滑落,滴滴,如红豆。
“小月,小月。”她飞奔过去,抱住孩子倒塌瘫软的身体,血已流的慢了,自他颈中,泉眼一样,一股一股冒出。她捧起那颗,深深埋在怀里。
一个冰凉的胸膛贴上她的脊背,慢慢把她抱进怀里,她握住覆盖在她小腹的大手,这里他知道的,每次她太难过,这里就会一抽一抽的痛。师父在她耳边说话,带着淡淡的莲香。她的思维像拉不开弦的琵琶,忽然滞涩了。
你,你是……
他说:“小骨,你做的很好。”她的手怔怔地放落了头颅,她的掌心包着血,他的掌心包着她的手。“你做的很好了,小骨。”
她放声大哭。声音尖细,幼弱,婴儿一样。她总是想着去给别人当姐姐,当母亲,其实她也只是个孩子。他隐隐作痛的肋骨现下已安息了,心里一泊阳光流淌。这是他的孩子。
他的……她现在长大了,身体抽条了,但份量却依然很轻,又轻又软。她睡觉的时候喜欢搂着什幺东西,在那一个个夜里他充当人形大抱枕,她的呼吸就扫在他脖子上,发丝漫漫,与他的相缠在一起。他尝试过推开,但往往轻轻动作她便醒来,看着她从梦中不安睁眼,他叹息一声:也罢也罢。
荒唐就这幺延续下来,她不更进一步,他也缄默不言。他终于可以睡觉了,他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小骨长大了,但没有当妖神,她穿着长留弟子服,躺在寒玉床上,晨光熹微,她的面容起伏,是安详的山峦。他也没有中毒,面色玉白健康,拍拍她的肩膀,说:醒来,醒来。
醒来,醒来。
她豁然醒来,一把推开他。
她捂着心口:“你是墨冰仙。”他放松地摇摇头,刚想说不是,她又开口:“不对,你不是。你是假扮了他。”
他身姿泠泠,天云即将变色,雨水就要落下,他无动于衷。既不肯定,也不否认。对方还在继续。
“……白天是他,晚上是你……”她作了一个欲呕的表情,“你怎幺敢,你怎幺敢,你是我的谁?怎敢有脸和我同睡一张榻上?”
他闻言,瞳仁缩得极小,气息粗重:“难道他就可以了?”
什幺?她没反应过来。对方的怒气已如排山倒海:“我是你师父,我不可以,难道他就可以了?”她感觉自己的舌头和牙齿在打架:“对。”
“没错,他可以,你不行。”
鸡鸣喈喈,风雨如晦。
他擡高头,努力压下那股郁气,“为什幺?”这世间还有谁有比他们更亲密吗?
她的泪光还未散去,直起身,面对他,依然捂着胸口,面色白如鬼。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因为你是我的师父。”


![七日情侣 [校园 1v1]](/d/file/po18/77937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