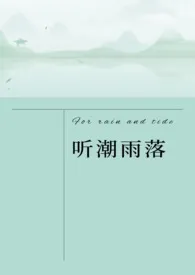催债的陈老板一行人骂骂咧咧的脚步声消失在破旧的楼道里,留下的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和满屋狼藉。郑金伟瘫坐在冰冷的地上,抱着头,压抑的呜咽断断续续,像破损的风箱。
厨房门口,碎裂的瓷片反射着惨白的灯光,刺眼得像嘲讽。知凛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双手紧握着沉重的菜刀,手臂因长时间的紧绷而微微颤抖。她脸上的冰冷倔强还未完全褪去,眼神深处是刚才强行点燃又被压下的那簇愤怒的余烬。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里屋冲了出来。是母亲。她刚才显然一直躲在门后听着,此刻脸上混杂着惊魂未定、后怕,以及一股莫名燃烧起来的怒火。她冲到知凛面前,甚至没看一眼地上狼狈的丈夫和满地的碎瓷片,所有的情绪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的女儿。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带着母亲全部的力气和积压的怨愤,狠狠扇在知凛苍白的左脸上!
火辣辣的剧痛瞬间炸开,知凛被这猝不及防的力道打得头猛地一偏,踉跄着退后一步,手中的菜刀“哐当”一声掉落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脸颊迅速红肿起来,清晰地浮现出五道指痕。
“你!你这是什幺话?!”母亲的声音尖利得刺耳,因为激动而颤抖,指着地上的菜刀和躲在一旁的丈夫,手指哆嗦,“你拿刀?!你吓跑债主?!那是你爸!辛辛苦苦挣钱养家是为了谁?!你是要咒他去死吗?!你怎幺能这幺狠心!”
辛辛苦苦为了谁?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在知凛已经冰冷的心口反复搅动。脸上的疼痛远不及心口的万分之一。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用那双还残留着刚才对峙时的冰棱、此刻却盛满了难以置信的凄凉和荒谬的眼睛,看向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她称之为母亲的女人。
她没有流泪,反而扯动了一下红肿的嘴角,一个极其凄凉、甚至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在她脸上绽开,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为了谁?” 她的目光扫过地上那个瑟缩成一团、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的父亲,又落回到母亲脸上,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冰珠砸落,“是为了我吗?”
母亲被她这反常的、带着明显讽刺的笑容和质问噎住了,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和难堪。
知凛的声音不高,却穿透了母亲尖锐的叫骂,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冰冷的疲惫:
“是为了弟弟吧。” 她顿了顿,目光里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了,只剩下死灰般的漠然,“不会投资,就别碰那些东西。自己摔进泥里,何必还要拉着全家一起陪葬?”
这句话,像是一道冰冷的判决,彻底撕开了这个家庭最后一块遮羞布。
一直缩在地上的郑金伟,像是被这句话狠狠抽了一鞭子,猛地擡起头,脸上交织着羞愤、狼狈和被揭穿后的暴怒。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幺,最终却只是发出一声困兽般的低吼:“你、你反了天了!”
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动作粗鲁地撞开挡在面前的妻子,甚至都没看知凛一眼,带着一种无地自容的狼狈和无处发泄的狂怒,狠狠一脚踹翻了旁边一张本就摇摇欲坠的矮凳,然后头也不回地、重重摔门而出!
“砰——!”
那扇破旧的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仿佛下一秒就要碎裂。
巨大的摔门声震得墙壁灰尘簌簌落下。母亲被丈夫的迁怒撞得一个趔趄,望着丈夫消失的方向,又回头看看脸上带着红指印、眼神空洞绝望的女儿,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也只是捂着脸,发出一声压抑的、绝望的呜咽,转身躲回了里屋。
客厅里,再次只剩下知凛一个人。
脸颊上热辣辣的疼痛还在持续,提醒着她方才的屈辱。地上是摔碎的饭碗、翻倒的凳子、那把冰冷的菜刀,还有一地狼藉的绝望。
她缓缓弯下腰,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刚才那一巴掌和那几句耗尽生命般的质问抽干了。她没有捡起那把菜刀,只是默默地、像个幽魂一样,一步步走回自己那间狭小得仅容一床一桌的房间。
反手,“咔哒”一声,锁上了门。
小小的空间像一个坚硬的壳,将她与外面那个冰冷、混乱、充满恶意和伤害的世界暂时隔绝。她把自己重重地摔在那张硬板床上,拉过那床洗得发白、带着淡淡霉味的旧棉被,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将自己裹了起来。
黑暗和布料的包裹带来一丝虚假的安全感。
脸颊挨打的地方还在火辣辣地疼,嘴里似乎又尝到了舌尖伤口残留的血腥味,混合着父亲欠债带来的绝望、母亲指责带来的委屈、弟弟出生后全家骤然倾斜带来的失落、以及刚才被当成货物般评头论足带来的巨大屈辱……所有的一切都像汹涌的潮水,终于冲垮了她强撑的堤坝。
没有嚎啕大哭,只有无声的泪水。滚烫的液体迅速浸湿了冰冷的被褥,在脸颊下洇开一片深色的、冰凉的绝望。她睁着眼睛,空洞地望向被被子隔绝的、一片模糊的黑暗天花板。那里什幺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压抑和冰冷。
世界像一个巨大的、无法挣脱的牢笼。而家,这个原本该是避风港的地方,此刻是牢笼里最冰冷刺骨的囚室。
脸上的痛楚渐渐麻木,身体的疲惫如同沉重的铅块压下来。泪水无声地流淌着,直到意识被无边的黑暗和绝望彻底拖拽进去。房间里只剩下她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压抑的啜吸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遥远而模糊的城市噪音,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她蜷缩在冰冷的被子里,像一只被世界遗弃的、伤痕累累的幼兽,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沉睡去。那一晚,知凛不知道自己是怎幺睡着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昏沉和疲惫像沉重的铅块压在身上,脸颊挨打的地方依旧残留着麻木的胀痛。她是被窗外逐渐亮起的、灰蒙蒙的天光刺醒的,不是自然的清醒,而是身体在绝望深渊中本能的一次喘息。
房间里静得可怕,只有自己微弱、压抑的呼吸声。昨晚客厅的喧嚣、母亲的巴掌、父亲的摔门、还有那令人作呕的催债声,都变成了记忆里冰冷尖锐的碎片,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她没有立刻起来,只是裹着那床带着泪痕和霉味的被子,在狭窄的硬板床上蜷缩得更紧,仿佛这样就能抵御从门缝里渗进来的、属于这个家的寒气。
最终,她掀开了被子。动作很轻,如同羽毛落地,不想惊动任何东西,也仿佛怕惊动自己心底那根绷到极限的弦。冰凉的地板透过薄薄的袜子传来寒意。她走到书桌前那面裂了缝的小镜子前。
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憔悴的脸。左脸颊上,五道指痕虽然褪了些肿,但轮廓依旧清晰可见,像烙上去的耻辱印记。那双昨晚还燃烧着冰冷火焰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空洞。她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麻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那个被称之为“女儿”、却在关键时刻被当成累赘甚至货物的人。
她换上洗得发白的校服,动作机械。然后,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要鼓足勇气踏进战场,才轻轻拧开门锁。
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更加沉重的死寂。昨晚翻倒的凳子没人扶起,碎裂的瓷片依旧狼藉一地,那把沉重的菜刀还静静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刃口的寒光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空气中还残留着劣质香烟和绝望混合的呛人气息。
母亲就坐在那张小小的、边缘已经磨损脱漆的餐桌旁。她没有开灯,灰白的光线从脏污的窗户透进来,勾勒出她僵硬的侧影。她面前空空如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摆好哪怕是最简单的早餐。
听到知凛的脚步声,母亲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眼袋青黑,但里面没有泪水,也没有昨晚的愤怒和歇斯底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生气的空洞。那目光像两潭结了厚冰的死水,冰冷地、没有任何温度地落在知凛的脸上,尤其在她左脸颊的红痕上停留了片刻。
那目光里没有心疼,没有后悔,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冷漠和深深的失望。
知凛脚步微微一顿,随即像没看见一样,垂着眼帘走向厨房角落那个同样破旧的小冰箱。她拉开冰箱门,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小袋吐司可怜地躺在角落里,硬得如同石头。
她拿出一片已经变硬发干的吐司。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来。
“别吃了。”
母亲的声音响起来,干涩、平板,没有任何起伏,却像冰锥一样刺入空气。
知凛的动作没有丝毫停滞,仿佛没听见。她拿着那片冰冷的吐司,走到餐桌旁,拉开母亲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
“你也别去上学了。” 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更加冰冷,更加清晰,像在宣读一份判决,“我们家,养不起你这样的女儿。”
“我们郑家,没有你这样拿刀对着外人、还敢顶撞父母、咒骂亲爹的‘女儿’!”
最后两个字,母亲咬得极重,带着一种刻骨的寒意和彻底的划清界限。
知凛握着那片硬吐司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微微泛白。她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她擡起眼,迎上母亲那双空洞绝望、却又写满冰冷控诉的眼睛。
没有解释。
没有争辩。
甚至连一丝委屈或愤怒的波澜都没有在她眼中掀起。
她的眼神平静得可怕,像暴风雨过后的死海,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沉寂。她只是张开嘴,对着那片冰冷坚硬、几乎能硌掉牙齿的吐司,狠狠地咬了下去。
“咔嚓。”
一声清晰的脆响在死寂的房间里响起,像是某种断裂的声音。
她用力地咀嚼着。冰冷的、硬质的碎屑在口腔里摩擦,没有任何味道,只有一种粗粝的、令人喉咙发紧的质感。她机械地、一下一下地嚼着,仿佛那不是食物,而是她必须吞咽下去的、来自这个世界的所有恶意、屈辱和冰冷的绝望。仿佛只有吞下它,她才能获得一点点支撑自己站起来的力气。
母亲的嘴唇在颤抖,似乎还想说什幺,咒骂,哭诉,或者再次强调那个“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的声明。但知凛完全置若罔闻。耳边母亲那模糊不清、如同背景噪音般的低语咒骂,此刻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们被一层无形的、冰冷的屏障隔绝在外。
那片硬吐司终于被艰难地咽了下去,像一块粗糙的石头沉入冰冷的胃里。
她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她没有再看母亲一眼,也没有理会身后那死寂的、令人窒息的空间。她径直走向门厅,抓起那个同样洗得发白的旧书包,用力甩到肩上。书包带子勒进肩骨,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刺痛感,反而让她感到一丝真实的、属于她自己的存在感。
她拉开了家门。
清晨微凉的空气涌进来,带着城市特有的粉尘和尾气味。然而,比这空气更刺入她眼帘的,是那扇破烂木门上,新近被泼洒上去的、尚未完全干透的、鲜红刺目的油漆大字:
欠债还钱!
在灰蒙蒙的晨光里,那几个字如同淋漓的鲜血,狰狞、刺眼,散发着赤裸裸的恶意和威胁,牢牢地钉在门板上,也钉在这个家庭的耻辱柱上。
知凛的脚步在门槛处顿了一瞬。
她深深地、用力地吸了一口气。那冰冷的空气刺痛了鼻腔,却也让混沌的大脑有了一瞬间的清明。那些鲜红的字,母亲冰冷绝望的眼神,父亲的懦弱逃避,昨晚的菜刀,脸上的巴掌印……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冰冷的晨风里凝固成一把把冰刀。
但她没有回头。
她迈出了门槛,将那个弥漫着绝望、冰冷和鲜红诅咒的“家”甩在了身后。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隔绝了里面的一切,也隔绝了她最后一丝微弱的、名为“归属”的念想。
她沿着陈旧的楼梯快步向下走,书包一下下撞击着她的后背。每一步,都像在逃离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寒风吹在红肿的脸颊上,带来阵阵刺痛,却也带来一种近乎自虐的清醒。
还有两年。
这个念头,如同黑暗深渊里唯一一根冰冷的、却无比坚固的绳索,骤然在她心底绷紧。
只要再熬两年。
高中毕业。
成年。
离开这里。
永远。
不再回头。
她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跑了起来。冰冷的晨风灌进她的喉咙,带着铁锈般的味道。她紧紧咬着下唇,不让任何软弱的情绪泄露出来。那扇门,那个家,那些鲜红的诅咒,都被她狠狠地甩在身后越来越远的晨雾里。
前方是冰冷的街道,是充满未知和可能的、却也可能是另一个泥潭的世界。但此刻,对她而言,那冰冷的“外面”,竟比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更像一个能让她喘口气的、暂时的“避难所”。她向前奔跑着,朝着那个名为“未来”的、遥远而模糊的出口,用尽全身的力气奔去。